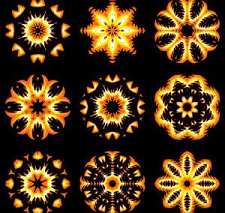太虚大师唯识学思想探索
发布时间:2020-04-29 15:34:48作者:佛心网
【内容提要】太虚大师对唯识学倾注了很大精力。但他与“南欧北韩”诸学派在学术关注点上明显不同。唯识学不仅是太虚大师一生关注和研学的重点教理,为此,他阐述了颇具特色的新唯识学,力主唯识学应成为真实应化的佛学,应将教与观相结合,不能有所偏废,为此,他撰写《唯识观大纲》,发掘基大师《大乘法苑义林·唯识章》之五重唯识观。阐发诠释唯识学三性说之精微之义,以作评价与阐释佛学各宗教理基础。并以此对应来自支那内学院派与日本佛教界的近代疑经之风,以维护经典的权威与神圣。
【关键词】唯识学 太虚大师 融贯 应用
唯识学一般而言是属于经院哲学的范畴,其理性思维和抽象性的特点,使人们总以为其与佛教具体修学实践及日常佛化的生活无甚密切关涉。但是,太虚大师对于唯识学在近代的弘扬,并成就其显学之位,居功甚伟,其关键点在于他之所以启绝学于再生,乃是为施悬壶以济世。帮助众生通过唯识学,认识到束缚众生解脱的最大之障碍在于心识的妄执,而妄执的根本,在唯识学中得到了透彻而深刻的剖析。因此,唯识学在太虚大师那里,成为其济世本怀的理性基础。
一
考察大乘唯识思想的源流,虽有由心所造、即心所现、因心所生、映心所显、随心所变等进入唯识理路的差别,从佛教教理史的角度考察,也有逐渐引发、各别深入研究的次第。但瑜伽行派精巧博大、恢弘缜密的唯识学体系,也是在上述思想的碰撞、磨合中走向成熟的。当然,唯识学以后所形成的学派分歧,也是因为后代唯识学派虽都在融贯上述五种唯识思想,但不无偏重的发挥,因此成为思想不同的学派。
当代佛学泰斗印顺导师在其名着《唯识学探源》中,对唯识思想有着深刻而精辟的论断:“有认识论上的唯识,有本体论上的唯识。我们所认识的一切,即是识的影像,这是认识论上的唯识。至于宇宙人生的本体,是否唯识,却还有问题。有人虽主张认识中的一切,只是主观心识的影像,但对认识背后的东西,却以为是不可知,或者以为是有心有物的。假使说心是万有的本体,一切从此出,又归结到这里,那就是本体论上的唯识了。这本体论的唯识,在认识上,却不妨成立客观的世界。佛教的唯识,当然是出发于认识论,又达到本体论的。到了本体的唯识论,又觉得所认识的有它相对的客观性,这才又转到认识论上不离识的唯识了。部派佛教里,没有本体论上的唯识学,认识上的唯识无境,却已相当的完成。”“唯识思想的成熟,主要是佛弟子们依着止观实践,而获得随心自在的事实证明。理论上,从非断非常的业感缘起的探讨下,展开了细心、细蕴、真我的思想,能为因性的种习随逐的思想。因大众、分别说、譬喻师的建立业因业果在心心所法的关系,心与种习结成非一非异的融合,完成唯识思想的一面。”“任何学派,没有不承认我们认识的不正确,没有见到真理的全面,或者根本没有认识。佛教的生死轮回,就是建立在一切错误中的根本错误上──无明。它障碍了真智的显现,蒙蔽歪曲了事理的真相,使我们在虚妄的认识下,颠倒造业,流转生死。所以要解脱生死,就要看透我们的根本妄执。在这点上着力,才能突破生死的罥索,得到解脱。要知道什么是错误的认识,就要研究到我们究竟认识些什么?这些不是真相,那真相又是什么?在这样的要求下,认识论就发达起来,引出了妄识乱现的思想,外境无实的思想,这又完成唯识学的另一面。等到这细心、种子,与无境的思想融合,唯识学也正式完成。”[1]印顺导师的论述,即把握了唯识学形成的脉络,也指正了唯识学在佛法体系中的作用,说明了唯识学之理的教证、理证及行证的理路。太虚大师的唯识学思想所具有的新型、融贯的特点,即表现为将唯识从经院哲学的象牙塔中解放出来,启绝学于再生,施悬壶以济世。使精致的、为一向不注重、或者说不擅长抽象思维和严密理论体系架构的中国佛学界所重视的唯识学,能够为众生所普遍接受,并晓以“要解脱生死,就要看透我们的根本妄执。在这点上着力,才能突破生死的罥索,得到解脱”之根本。
正因为唯识学是涉及到认识论、本体论这两大哲学重要命题,所以,在近代佛教的复兴中,有志振兴弘扬佛法者,都无法绕过这一佛学重要教理体系。以太虚大师为代表的武昌佛学院,与以欧阳竟无居士为代表的支那内学院、以韩清净居士为代表的北京三时学会,都以唯识学的研究、传播、弘扬为其要务,使自玄奘法师以后几成绝学的唯识学经院哲学体系,在民国这一纷繁的时代,一变而为一时显学。同时,三位唯识大师及其所形成的学派,在唯识学研究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形成近代唯识学的三系。太虚大师一系的唯识学,以出家僧众为主,在价值取向、治学方法和理论体系的建构方面,与其他两系既有共同的特点,又有明显的差异。唯识学,不仅是太虚大师一生关注和研学的重点教理,而且,是太虚大师诠释佛学各派思想、评价与阐释各种文化思想的主要佛学教理基础。同时,唯识学在太虚大师那里,也是作为出家僧,对应来自支那内学院派与日本佛教界的近代疑经之风,以维护经典的神圣性的护教之重要依据。
最为重要的是,太虚大师的唯识思想,在其所倡导的“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等三大革命的思想体现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是其具体的佛法实践在理论层面上的总结和提炼。这是由中国国情环境下的宗教实际所决定的。中国的宗教问题,受到历代皇权绝对专制传统所左右、钳制,世间的一切,包括出世间的宗教须隶属依附于皇权,并自觉成为帝王维系皇权统治的工具。由此,宗教根本无真正独立自主发展的空间与土壤。当然,中国宗教自身也一直存在严重的信仰利性与信仰世俗化问题。所谓“临时抱佛脚”,即为中国民众对信仰的功利主义心态最为生动形象的写照。而出家僧道人士,诚意修学求道者寥如晨星,多为在经忏中讨寻求生计之辈。由此才有太虚大师在民国期间立志革除佛教弊端,改革僧伽制度,建立一种现代新型人间佛教的理念涌动。他改革的重心就在于,“一、对僧团人数力求减少,重质不重量,除伪显真。二、偏重信众,以建设一菩萨学处,以广摄社会青年归依三宝。三、以人成即佛成之人生佛教为终极”。[2]而唯识学作为佛法对世间诸法之认识论、本体论的系统诠释,在太虚大师的“三大革命”中,担当了思想基础与理论源泉。
根据太虚大师对佛教的分类,大乘佛教体系可以分为法性空慧学、法相唯识学、法界圆觉学三系。其中法相唯识学是重要一系。太虚大师学术思想命脉的承续者印顺导师在其前辈的基础上,又以更为精确、清晰的定义,将三大系命名为性空唯名论、虚妄唯识论、真常唯心论。如果不算初学启蒙,太虚大师实际上是自一九一五年开始,对唯识学理论进行长达两年的系统学习和研究的,他的主要唯识学著作也大多在此后才逐步问世。印顺导师在《太虚大师年谱》中叙述到:“是年夏起,专心于楞伽、深密、瑜伽、摄大乘、成唯识论,尤以唯识述记及法苑义林章用力最多,将及二年之久”。[3]太虚大师留下了很多唯识学著作。据印顺导师所编辑的《太虚大师全书》收录,自十四至十八册,共计有专着十八种,论文三十一篇。其中,有关法相唯识学属于论点诠释的著作有:《解深密经如来成所作事品讲录》、《深密纲要》、《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讲要》、《瑜伽真实义品讲要》、《瑜伽师地论菩萨地真实义品亲闻记》、《辨法法性论讲记》、《辨中边论颂释》、《摄大乘论初分讲义》、《新的唯识论》、《唯识三十论讲录》、《唯识三十论讲要》、《唯识三十论题前谈话》、《唯识讲要》、《唯识二十颂讲要》、《大乘五蕴论讲录》、《八识规矩颂讲录》、《大乘法苑义林唯识章讲录》、《因明概论》等;有关法相唯识学教义诠释的著作有:《法相唯识学概论》、《百法明门论宇宙观》、《阿陀那识论》、《末那十门三世与赖耶十门二位之同异》、《能知的地位差别上之所知诸法》、《人心所缘有为现行境之本质与影像关系》、《阅“相见别种辨”》、《见相别种辨释难》、《种子法尔熏生颂》、《为无为漏无漏对观颂》、《唯识诸家会异图》、《四大种之研究》、《阴蕴之研究》、《法与人之研究》、《谈唯识》、《唯识观大纲》、《遣虚存实唯识观之特胜义》、《唯识之净土》、《兜率净土与十方净土之比观》、《慈宗的名义》等,有关融贯法相唯识学与其他佛学教义体系,并比较抉择的著作有:《佛法总抉择谈》、《三重法界观》、《对辨唯识圆觉宗》、《起信唯识相摄图》、《大乘起信论唯识释》、《答起信论唯识释质疑》、《竟无居士学说质疑》、《论法相必宗唯识》、《释会觉质疑》、《再论法相必宗唯识》、《阅“辨法相与唯识”》等。
如此众多的唯识学著作,在中国佛教史上,直追中国唯识学的传承者和弘扬先驱真谛、玄奘大师,以及玄奘大师门下的窥基、圆测大师,而在近代佛教复兴浪潮中,也只有欧阳竟无、韩清净、吕澂、王恩洋居士能与之比肩。
二
正如印顺导师所认为的那样,太虚大师的唯识思想与学术理路,与上述的同辈有不同的视角和切入点。
太虚大师所处的时代,是中国近代佛教思想极其活跃、教理探索异常丰富的时期。其中,唯识、心性、如来藏思想及其相互关系,始终是佛学思想研究和论争的焦点。耐人寻味的是,唯识、心性与如来藏思想融合而成的作为传统中国化佛教核心范型的心性如来藏思想渐渐成为佛教批判的对象,如支那内学院系欧阳竟无、吕澂、王恩洋以及汉藏教理院系的当代高僧、佛教僧界学术大师印顺导师等,即分别依据唯识学与中观学立场,有深刻的审察与批判。在建立现代佛教学术研究规范的日本佛学界、印度学界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兴起“批判佛教”思潮,不仅对心性如来藏思想,而且对唯识学,予以猛烈的批判,乃至否定。由此可见,中国佛学界之所以选择唯识学作为现代佛学复兴的理论引子,是有其深意在内的。太虚大师就此发表众多的著作和讲演稿,也是具有极强的针对性的。
说到太虚大师的唯识学思想,必须将其放在与另两位唯识学大师欧阳渐(竟无)居士和韩清净居士的比较中,方能準确把握。欧阳竟无居士的唯识学,最突出的一点是分唯识与法相为二门,这一分法尽管佛学界至今尚未公认,但其影响却不可小视。欧阳竟无居士认为,属唯识门的经论,有无著的《摄大乘论》,世亲的《唯识二十论》,天亲的《大乘百法明门论》,护法的《成唯识论》。属法相门的有安慧的《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世亲的《大乘五蕴论》,无著的《大乘庄严经论》和弥勒的《瑜伽师地论》。他确认法相与唯识比较而言,法相广于唯识,唯识精于法相。法相门立五法义和三自性义,五法是相、名、分别、正智、如如。“相”是森罗万象的有为法的相状;“名”是相的理论概括;“分别”是执虚妄的“相”、“名”为实有之分别心;“正智”是佛智;“如如”是依正智而证得的真如。三自性是遍计所执自性、依他起自性和圆成实自性。唯识门立八识和二无我义。八识即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赖耶识;二无我也叫二空,我空和法空。欧阳竟无又说:法相门讲非有非空,而唯识门之“唯”,破心外有境,指法空,“识”则破心空,破斥对空之执着而讲破空执之有。法相讲诸法平等,唯识讲万法统一。在印度诸师中,欧阳竟无认为无著是弘唯识门,胜军也弘唯识,弥勒则先创法相门,后创唯识,戒贤是弘法相门。玄奘在印度,是从戒贤学法相,从胜军学唯识。在法相门和唯识门中,先生似更推崇唯识门,他认为“唯异生、圣人,以唯识判;唯外道、内法,以唯识衡;唯小乘、大乘,以唯识别”[4]。凡圣之别,内外之异,大小之分,都要以唯识为準则。对于唯识门中的阿赖耶识,先生给予了详尽分析,指出其含有持种心、异熟心、超生体、能执受、持寿暖、生死心、二法缘、依识食、识不离、染净心这十理,指出此识深细不可知,指出不为声闻乘人立此识,等等。先生认为法相一门最终归于唯识一门,故此两门又可总称唯识学。欧阳竟无先生最终的学术思想是立无余涅槃三德相应、瑜伽和中观融于一境、以佛学融摄儒学的三大思想。
欧阳竟无、吕澂、王恩洋居士将其学术兴趣和研究重点放在法相与唯识的抉择,唯识义理的发微之上的;而且在弘扬唯识的同时,对各教派进行了批判直至于否定;所以,支那内学院派法相唯识学更多表现为抉择与回归追索唯识学的学术原生态。特别是该学派通过对法相唯识学发展历史的梳理研究,提出唯识和法相在理论上具有不同特点的两种学理的崭新见解。反映在《瑜伽师地论》中,“本地分”详诠法相,“抉择分”阐明唯识。以后,“无著括《瑜伽师地论》法门,诠《阿毗达磨经》宗要,开法相、唯识二大宗”[5]。具体说来,以《瑜伽》为本,“抉择于《摄论》,根据于《分别瑜伽》,张大于《二十唯识》、《三十唯识》,而胚胎于《百法明门》,是为唯识宗”。“抉择于《集论》,根据于《辨中边》,张大于《杂集》”,“而亦胚胎于《五蕴》,是为法相宗”[6]。欧阳竟无先生在有关的经论叙着中,多次从不同角度比较法相学与唯识学之间不同点。对此,太虚大师明确质疑法相唯识非一说,坚定认为:“凡属遮表言思所诠缘者,无非法相,一一法相,莫非唯识。故法相所宗持者曰唯识,而唯识之说明者曰法相。”[7]值得一提的是,民国初年著名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则高度称赞竟无先生的创见,在其《支那内学院缘起》一文中,对于竟无先生的论点感慨到:“余初惊怪其言,审思释然,谓其识足以独步千祀也。”
韩清净居士为代表的北京三时学会派的特点,则不在于对唯识义理的总体把握,而是将学术的重点放在对唯识学基本论点的逐字逐句考证辨析。他所著的《瑜伽师地论科句披寻记》、《唯识三十颂诠句》、《成唯识论讲义》、《大乘阿毘达磨集论别释》、《解深密经分别瑜伽品略释》可见其学术之意趣与欧阳竟无居士等不同之处。直到当今时代,韩镜清老居士化毕生精力撰就的煌煌巨着《成唯识论疏翼》,即是三时学会系唯识学治学传统的典范。故东初法师在其所著的《中国佛教近代史》中感慨到:“韩氏不唯精于《瑜伽》、《摄论》,且能熟背。他讲《摄论》,一字一句,皆交出来自《瑜伽》某卷某句。普通讲《摄论》,多则一年,少则半年,韩氏讲之,则非二年不可,以其精故,不能速也。”东初法师还评价南欧北韩之治学方法的差异,称韩清净说:“他治学的方法,迥异于竟无居士。竟无于唯识诸论,不在逐字寻求其来源,而在扼其大意。因此,始由唯识,而般若,终至涅槃,总扼其佛学之大纲。韩氏则采精兵主义,其于法相唯识学,旨在穷究瑜伽,然后旁及十支。所谓一本十支,故其学始终未能突出此一范围。”[8]由此可见欧、韩二氏于唯识之长短。
作为出家僧的唯识学大家太虚大师,则将重点放在以现代的语言解释铺陈唯识之义,“得唯识之善巧”,虽“多以法相唯识化众”,却与专宗唯识者“异也”[9]。李广良先生在其《心识的力量·太虚唯识学思想研究》专着中,将太虚大师的唯识学思想分为融贯的唯识学、新的唯识学和应用的唯识学,是比较全面準确的,把握了太虚大师唯识学的基本要点。李广良先生将太虚大师唯识学思想总结为“新”与“融贯”两大特点,在近代唯识学中系独树一帜的独特学说。
所谓融贯的唯识学,表明了太虚大师在努力弘扬唯识学之时,着力融会唯识学与各派佛学思想的思想方法,贯通各家佛学思想理路。但佛学上的宗派、学派,都是对于佛陀一生弘传的大法理解上的深浅、宽狭,修学上的方法之差别,以及为适应众生的根机利钝、教化时机因缘之区别,而作出的不同的诠释与阐述。实际上,作为由佛陀一脉相承的佛教各宗派、学派,其义趣、目标并无根本之分歧。因此,门户之见、褒贬毁誉都为根本佛法所不容,与佛陀本怀相违。中国传统政治忌讳结党,中国传统佛教也反对门户之争。太虚大师对佛教界门户之见乃至于门户相争深恶深恶痛绝。由此,他在唯识与判教、唯识与《楞严》、唯识与《起信》、唯识与法相等问题上,从护教的立场出发,发心消除门户之见、派系相争的陋习,由唯识的观点为基点,对各宗派的观点作了融贯。因此,所谓“融贯的唯识学”,既有对治中国佛教界门户之见的融摄,主要表现为太虚大师“八宗齐弘”的理念,以及提出法性空慧宗、法相唯识宗、法界圆觉宗三系组织,以架构大乘佛学体系,恰当明确法相唯识宗的地位;同时又有融会唯识学与各派佛学思想,在强调唯识宗与他宗平等性的基础上,又用唯识学的义理去阐释、充实和丰富各宗派的思想。其中,针对欧阳竟无内学院派对《楞严》、《起信》的伪经伪论之分析判断,起而维护《楞严》、《起信》经论的真实性与经典权威,以唯识学学理诠解《楞严经》和《起信论》,疏解唯识理论和《楞严》、《起信》学理的矛盾;又针对欧阳竟无先生分法相、唯识为二学之论,着力辨析唯识与法相之关系,特别强调“法相以唯识为宗”的理念。
太虚大师唯识思想的重要组成,是他提出的“新唯识学”体系。《新的唯识论》于一九二o年问世。太虚大师之所以提出“新唯识学”之概念,是基于随着二十世纪的到来,人类在充分享受科学成果的同时,对科学的迷信也随之在人类社会弥漫,哲学成为科学的附庸,唯物主义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普遍认同的事实。实际上,哲学成为科学的附庸,比之哲学作为神学的附庸,将给人类带来更多意想不到的灾难。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太虚大师,与英国哲学、数学大师罗素一样,已经痛切地感受到缺失信仰与精神因素的科学,是人类的灾难之源,而唯物主义的重大失误就是精神的缺位与依附物质。因此,太虚大师提出:“迫于人智之要求所不能自己,大乘唯识论乃应运兴起。且彼时虽有小乘之正论,徒高超世表而不能普救群生,与今日虽有科学所宗依之近真唯物论,徒严饰地球而不能获人道之安乐,亦恰相同。故唯识宗学,不但与唯物科学关通綦切,正可因唯物科学大发达之时阐明唯识宗学,抑亟须阐明唯识宗学以救唯物科学之穷耳。夫然,亦可见新的唯识论之所以为新的唯识论矣。”[10]以新唯识论而起悬壶济世之功,弥补唯物主义和科学迷信的片面,是太虚大师的理想。新唯识论之“新”,太虚大师虽未加以定义,但《新的唯识论》通篇都在阐述这个问题。
说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哲学命题,一般国人都赋予其政治内涵,实际上,必须明确的是,首先这不是一个政治概念,并非评判意识形态是非的标準,而仅仅是西方哲学两大不同的流派,是对世间一切存在的两大不同解释角度而已。其次,要明确的是,佛法所倡导的“一切唯心所造”教义,属于认识论范畴的命题,是一种对于人们心灵之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认识作用、影响力度的体现;而西方哲学史上的唯心唯物阵营的划分,则是建立于本体论的基础之上,是对宇宙万物起源的两大迥异的观点。对此不同范畴的命题,切不可混淆,更不可因而否定佛法强调“心”之作用,注重“心灵”调伏对于世间和谐所发挥的积极意义。
在《新的唯识论》八个组成部分中,其中有七个部分,是对唯识性质的分析,太虚大师将唯识学分类表述为宇宙的人生的唯识论、分析的经验的观察的系统的唯识论、转化的变现的缘起的生活的唯识论、真理的实性的唯识论、悟了的解放的改造的进化的决择的唯识论、实证的显现的超绝的胜妙的成功的唯识论、究竟的唯识论。太虚大师以清晰的学者笔调、严谨的理论辨析、平实问答的弘教方法,将唯识学的社会功能、根本性质、济世作用作了深刻而浅显的表述。所以,虽然大师未对唯识之“新”作出明确的定义,但通篇的叙述,可以将新唯识学归纳为系一种真的、适应并化度众生的唯识论:“新的唯识论,即真的唯识论之应化身也。从真起应,全应是真,虽真应一宗,而时义之大,贵在应化。此诚鸿伟之业,吾亦聊尽其粗疏棉薄之力,为智者之前驱而已。”这里不仅说出了新唯识论的特征,也表达了太虚大师对他所倡导的“佛教革命”的信念,其中也隐约地表达着他对“佛教革命”前途的悲观之愁绪。
对新唯识学理论的概括,主要有三项内容。首先,从表述形式上说,太虚大师以现代白话,对唯识学进行全新的诠释,发掘唯识学的微言深意。其次,着重于阐述唯识学的社会功能,发挥唯识学济世功能。最后,太虚大师以唯识学义理诠释诸种哲学与文化现象,其中以对唯心唯物的偏颇的双向质疑补正。总之,太虚大师将唯识学发掘为具有广泛适应性的文化诠释工具和价值判断体系,用以解读中国传统典籍,论证自由与革命,为人间佛教建立心性论基础,充分发挥了唯识学的认识论、存在论等哲学基础的价值。
三
太虚大师对唯识学的贡献首先体现为对“唯识”之义作了全面準确的阐述,稳固了“诸法唯识”的学理基础。重新架构了唯识学体系。众所周知,诸法唯识是唯识学的核心理论。成立诸法唯识,是唯识学立足于社会、说服信徒接受“一切唯心所造”基本理念,并为学术规范所认同的基本要点。为此,太虚大师在《法相唯识学概论》、《新的唯识论》等著作中,以全新的语言,对诸法唯识的思想进行了阐述。在《法相唯识学概论》中,太虚大师考察了易与唯识学相混淆的西方流行的主观唯心论、客观唯心论、意志唯心论、经验唯心论、直觉唯心论,并逐个加以分析批判,并由此对唯识理论体系进行重新组织,共分十四个问题进行阐述架构:一、虚实问题,解决独头意识与同时意识之关系;二、象质问题,解决同时六识与第八识变之关系;三、自共问题,解决自识所变与他识所变关系;四、自他问题,解决第八识见与第七识见关系;五、总别问题,解决八心王法与诸心所法之关系;六,心境问题,解决能缘二分与所缘三分关系;七,因果问题,解决第八识种与第七识现之关系;八,存灭问题,解决八识现与一切法种之关系;九,同弊问题,解决一切法种与一切法现之关系;十,生死问题,解决前六识业与八六识报之关系;十一,空有问题,解决诸法无性与诸法自性之关系;十三,凡圣问题,解决染唯识界与净唯识界之关系;十四、修证问题,解决唯识行与净唯识果之关系。唯识学理论体系,包括境、行、果。一般唯识学论典多由第八识、第七识、第六识的次序予以展开,如《唯识三十颂》等。这种由深至浅,由难至易的次第,往往拒非上根利机者以门外。但太虚大师的唯识学诠释,则是根据人们认识规律,由浅至深,由易至难,从六识到八识,从共不共变到自他形成,从现行果到种子因,从现象差别到生命差别,从染唯识界到净唯识界。层次分明,引人入胜,这种安排为研习唯识学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太虚大师对唯识学的贡献又表现为以三性抉择一切佛法,维护了中国各宗派存在的合理性、如法性,会通了《楞严》、《起信》,确立了《楞严》、《起信》在佛教体系中应有的地位。欧阳竟无先生撰写的名着《唯识抉择谈》,以唯识宗的立场斥责贤首宗、天台宗等为颟顸佛学之源,并认定《起信论》系中国佛教徒的伪造之作,与佛理不通,实属乖谬之典。太虚大师认为,欧阳竟无先生之论,系对一味平等佛法未能融会贯通之结果,乃依唯识学的三性思想,撰《佛法总抉择谈》,批判竟无居士的错误观点。
三性,不仅是唯识宗的基本理论,也系佛法之全体的属性。大师以三性抉择一切佛法。认为在三性中,仅仅略说依他起的浅相而未遣除遍计执相,是人天乘之罪福因果教;依据遍计我法执,以破遍计者之人我执,促其舍弃依他起相,是声闻乘的四谛教;至于不共大乘佛法,圆说三性无不周全圆融,但施设言教,应当遍于三性。一、依照遍计所执身自性,有针对性的施设言教,惟破不立,以扫蕩一切遍计执尽,证圆成实而了悟依他起。《十二门论》、《中论》、《百论》等般若为其代表,以一切法智不可得为其教理宗旨,以能起行趣证为其殊胜之用。二、依照依他起自性施设言教,具有应机性的破立,以依他起法的如实明了,达到遍计执之自行遣除及圆成实之自行证悟。《成唯识论》等唯识著作是其代表,以一切法皆唯识变为其教理宗旨,以理性的树立理而引发修行实证为其殊胜之用。三、依照圆成实自性施言教,对诸法唯立无破,以开示果地证得圆成实,令众生起信,当通达圆成实时,则遍计所执自然远离,依他起自然通达悟了。《华严》、《法华》等经,《起信》、《宝性》等论为其代表,以一切法皆真如为其教理宗旨,以能起信求证为其殊胜之用。
上述三者统摄涵盖一切法,无任何遗漏之点。但是,具体的施教方便中,各宗对于三性,其强调的程度是有差别的。般若学扩大遍计执性,缩小余二性,凡名想所及都摄入遍计执,唯以绝言无得为依他起、圆成实性。故此宗说三性,遍计固然是遍计,依他、圆成也是遍计。对此问题,宗喀巴大师在其《菩提道次第广论》中有比较详细的阐述,并在弥补此项弱点方面,作了很多学术架构,为藏传佛教中观学奠定了新的基础。[11]唯识学则扩大依他起而缩小余二性,以佛果有为、无为漏,及遍计执之所遍计,都摄入依他起,唯以能遍计而起的能所执为遍计执,无为体为真如。所以唯识学说三性,依他固依他,遍计、圆成也是依他。而真如学[12]则扩大圆成实性而缩小余二性,以有为无漏,及离执遍计,摄入圆成实,归真如无为之主,唯以无明杂染为依他、遍计执相。故此宗说三性,圆成固圆成,遍计、依他也是圆成。所以,以三性抉择一切佛法,是太虚大师在唯识学的应用方面的一大发现。以三性抉择,说明各宗理论虽立足点不同,但是却无予盾、更无对抗,水火不容、唇枪舌箭,实为对佛陀微言大意的误读所致。太虚大师的此种真知灼见,可谓前无古人;而其对唯识三性说的发挥,也可说开唯识学之先河之说。
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太虚大师八宗齐弘之理念的学理基础,也为合理评价《楞严》、《起信》之体系。太虚大师在分析了支那内学院派之观点后,依据自己对“三性”说诠释的结论与方法,对《楞严》、《起信》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太虚大师认定《楞严经》是中国佛学的大通量,未尝有一宗取为主经,未尝有一宗贬为权教,应量发明,平等普入。于是,大师结合自身的悟境,撰写了《首楞严经摄论释》、《楞严经研究》。沟通《楞严经》与唯识不同之处,为《楞严经》的弘扬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太虚大师分析认为,《起信论》所说的真如与唯识学所说的真如不同,唯识学的真如偏于理性的,而《起信论》的真如是包括理性与正智。而且,《起信论》虽然未说种子,其实已具足种子义。由此,《起信论》与唯识并不矛盾。太虚大师清醒地认识到,《起信论》代表着中国传统佛教思想,在汉传佛教中发挥着重要的教理基础和修学依止的作用,必须将其与唯识学做好会通,澄清误解,精心维护。
四
有道是,只有在实践之中的理论,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理论。唯识学也是如此,如果将其作为经院哲学,供奉于学术的象牙塔内,唯识学对于信仰的实践、修学的指导,以及对社会的作用等等生命力,将会被窒息、扼杀。对此,太虚大师有着深刻的认识,自身也有深切的体会。太虚大师对唯识学的贡献还表现为倡导教观合一,注重唯识学在修学上的实际应用性。从而间接地将本属纯学理性的唯识学作为其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的理论基础。
唯识学在一般学佛者中间,往往被视作系缺乏具体观行的理论,而在太虚大师看来,佛法是实践的宗教,系修学的笃实践行之道,因此,其理论都是观行的总结,观行都为理论的基础。就唯识学而言,大师写了《唯识观大纲》,立五种唯识观,通过深刻阐述和发挥唯识观的实践作用,提请国人以唯识之观、联系唯识之教,关注社会现实,关怀自身处境。
唯识宗虽然理论丰富,但在观法方面只有玄奘大师的及门弟子窥基大师的《大乘法苑义林·唯识章》中提出的五重唯识观,可是,恰恰是这部重要的阐述唯识观的著作,却在漫长的中国佛教历史上,不为教界与学界的重视,始终游离于学界的视野之外,又不为教界所重。这无疑印证了太虚大师对中国佛教现状的忧虑——大师的《评大乘起信论考证》中说:“日本人、西洋人治佛学者,丧本逐末,背内合外,愈趋愈远,愈说愈枝,愈走愈歧,愈鉆愈晦,不图吾国人乃亦竞投入此迷网耶!”究其原因,乃是因为“一切佛法,皆发源从释尊菩提场朗然大觉之心海中所流出,后来任应何时何机所起波澜变化,终不能逾越此觉源心海之范围外;此于佛法具信心者,任何人当靡不承认之者”[13]。因此,我们不能用西洋人治学方法来治佛学,应该依教起观,解行相应,否则终不能得到佛法真谛。这也确实击中了中国佛教界陋习之要害:一种人不重视教理学习,抓住一句佛号或一句话头便苦修终身;一种人虽终生学教,但只作为学问研究,甚至用考证方法妄议经论真伪,坏他信心。
所谓唯识五观,是依照唯识之教而指点的修学之道,窥基大师总结为:遣虚存实唯识观、舍滥留纯唯识观、摄末归本唯识观、隐劣显胜唯识观、遣相证惟唯识观;这些唯识观所针对的就是众生对虚、滥、末、劣、相的执着,要求众生通过唯识教之学习悟解,通过自身的存、留、归、显、证的观行,将其转化为实、纯、本、胜、惟。大师在阐述上述五重唯识观时,十分善巧地以五位百法的唯识观、依真有幻全幻即真的唯识观、悟妄求真真觉妄空的唯识观、空云一处梦醒一心的唯识观为铺垫,帮助众生进入唯识观,为最终修学五重唯识观奠定了基础。太虚大师深刻总结道:“上五重唯识观,总核其理性可约为三义:一、周偏计度为唯识之虚妄法,属妄执性,是应遣离者。二、依托他缘为唯识之世俗法,属缘起性,是应转净者。三、圆满真实为唯识之胜义法,属真胜性,是应开显者。就此三义,更可约留二法:一、世俗,二、胜义。而二法又各有四义,谓‘虚妄’、‘道理’、‘证得’:‘真实’是也。以此二法互融四义,第一重、为虚妄世俗,第二重、为道理世俗兼摄虚妄胜义,第三重:为证得世俗兼摄道理胜义,第四重、为真实世俗兼摄证得胜义,第五重、为真实胜义。所云‘虚妄’、是应离舍。‘道理’、是当了悟通达。‘证得’、是有修行,有成功者。‘真实’、是无对待,无变易者。随何一法,无不如是,诸法本性,是唯识性。循此观想,夫亦可以悟唯识而证真如矣。”[14]
唯识学的应用性、实践性在太虚大师的唯识观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
他生活于中国社会动蕩的岁月,他经历了世界两次惨烈的战争。久远的累世宿根将他引入玄妙的佛门,睿智的慧根让他肩负沉重的使命。生活于一八九o年至一九四七年的太虚大师经历了太多的人间沧桑悲凉、惨烈疾苦、世态变迁。如今,岁月又走过了一个甲子,六十年的历史,没有改变人类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太虚大师所为之痛心疾首的难题依然缠绕着中国佛教界。在此特殊的时刻,这位上世纪伟岸僧人的学术品味、人格魅力、思想理路,于我们的意义依然不减当年。
太虚大师一生的事业和学术活动,可谓波澜壮阔、博大精深、深邃无垠。因此,当代人要以个人的力量,把握其思想的脉络,精研发微,恐怕已经难以具备如此的深厚基础了。无怪乎大师的学生郭朋先生在完成《太虚思想研究》后,面对自己煌煌四十五万字的著作,还是要感慨只是在“述而不作”。本人此作连“述”亦尚未周全。不揣冒昧,谨此告慰大师含笑常寂光天之英灵!
[1]见《唯识学探源》,正闻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妙云集》版p200~201
[2]见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下册,台北:东初出版社一九七四年版p969
[3]见《太虚大师年谱》,正闻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妙云集》版p77
[4]《藏要·论叙》之《摄大乘论》,见《欧阳竟无内外学》甲函

[5]《世亲摄论释叙》,见《欧阳竟无内外学》甲函南京金陵刻经处线装版
[6]《法相诸论叙》,见《欧阳竟无内外学》甲函南京金陵刻经处线装版
[7]《竟无居士学说质疑》见《太虚大师全书》第十八册p1457
[8]见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下册,台北:东初出版社一九七四年版p671
[9]见《太虚大师选集?序》正闻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10] 《新的唯识论》,见《太虚大师全书》十六册p610-611
[11] 详见宗喀巴大师《菩提道次第广论》第三十二卷。
[12] 此派学术即是受到支那内学院派诘难最多的,印顺导师将其列在真常唯心之派系。
[13]《评大乘起信论考证》,见《太虚大师全书》四十九册p29
[14] 《唯识观大纲》,见《太虚大师全书》十八册p1353—1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