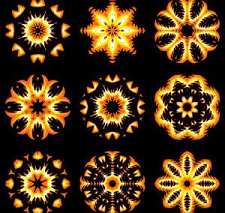它伴着云居寺而生,是北京第一批市级传统村落,故宫用这的汉白玉
发布时间:2024-07-26 04:05:01作者:佛心网作为一个村庄的名字,“石窝”使我眼前一亮。毫无疑问,这个字眼属于乡间俚语,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石头的老家或者石头的故乡,但都不如“石窝”更形象,更亲切,更富有通俗的韵味。2018年3月,在北京发布的第一批市级传统村落名单中,共有44个村庄入选,石窝村位列其中。一个与石头有关,又历史悠久的京西南古村落,一下子引起了我的兴趣。时隔半年,我又在《北京日报》看到一则消息——《石窝村史馆传承汉白玉文化》,便随手剪裁下来。就这样,一个参观村史馆、游走石窝村的计划产生了。然而,忙忙碌碌,一再拖延,直到几天前才终于成行。
作者 岳强
石窝村的工匠正在雕刻。 摄影:张玉军 供图TAKEFOTO
村史馆在村委会办公楼里,只有一间展室。我是一边上楼一边打听到那间展室的,展室的门开着,却空无一人。一位村干部问明来意后,叫来了一位女讲解员。女讲解员热情洋溢,像是在接待一位远方的客人。虽然展览是对外开放的,我仍感到自己有些唐突。为了表明对石窝村及汉白玉文化的兴趣,我从背包里拿出当初的剪报,那是2018年9月12日《北京日报》第5版的一角。讲解员嫣然一笑,示意我往墙上看,原来“结语”的旁边也贴着这份剪报,还加了一层塑料保护膜。也许是剪报消除了隔阂,她开始声情并茂地讲述石窝村的前世今生,尽管展室里只有我一个参观者。
展室布置得整洁而精致,主题为“精美的石头会唱歌”,除了《序言》和《结语》,还根据不同内容划分出了石之源、石之藏、石之技、石之艺、石之景和石之情六个展区,不大的空间被充分利用。展室的显要位置有一个硕大的金色“匠”字,旁边贴着十几张汉白玉艺术品的老照片。讲解员告诉我,那些汉白玉艺术品均出自石窝村老石匠之手,获得过各种奖项,体现了石窝人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从这里,我开始了解石窝村——这个伴着云居寺而生的古村。
1999年9月9时9分9秒,石经再度回归地穴封藏。 (资料照片)
云居寺与石窝村的源泉
先有汉白玉,后有石窝村。不论是储量,还是质地,抑或开采加工历史以及雕刻工艺,大石窝汉白玉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而石窝村是大石窝汉白玉的标志性产地。据《房山县志》记载:“大石窝在县西南四十里黄龙山下,前产青白石,后产白玉石,小者数丈,大者数十丈,宫殿营建多采于此。”这里所说的“大石窝”,就是现在的房山区大石窝镇石窝村。
石窝村以北大约五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千年古刹云居寺,这座坐落于石经山西南麓的古寺因石刻佛经而闻名于世。石经山古称白带山,因为那里的山体热,一下雨,山间便云雾缭绕,像是缠绕着一条洁白的带子。隋朝大业年间,幽州智泉寺僧人静琬吸取北魏、北周两次灭佛灾难中很多纸本、木刻佛经被焚毁的教训,继承其师遗愿,在荒僻的白带山开创了刊刻石经的千秋大业,意在使佛经永久保存。之所以把刻经地点选在白带山,一是因为这里距大石窝很近,可以为刻经提供充足的石料来源。二是当年的白带山山深林密,远离尘世喧嚣,便于僧人静修和刻经藏宝。
大量工匠、民夫和僧人聚集到白带山后,一个现实问题产生了。他们在荒山野岭中从事采石刻经作业,既没有可供食宿的房屋,也没有习经诵经的寺院,每天早晨从山下的住处赶到山间的工地干活儿,傍晚收工后,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各自的住处。日复一日的往返奔波,既耽误时间,又消耗精力,给刻经事业带来极大不便。于是,一个在白带山下修建寺院的念头在静琬的脑海中萌生了。然而,由于刻经的经费有限,这一想法暂时搁浅。唐贞观五年(公元631年)盛夏,暴雨引发山洪,杖引溪上游两岸崩塌,将上千棵巨大的松柏抛入溪中,随溪水漂流到白带山下。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些上好的木材使静琬如愿以偿。于是,云居寺诞生了。
云居寺创建初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佛教寺院,它所承担的一项重要职能是为采石刻经的工匠和民夫提供食宿。或者说,那是一座汉白玉开采的大本营。从文献记载看,静琬在白带山主持刻经时,采石、运石、磨碑、刻经以及将刻好的石经存入藏经洞,都有专人负责,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序。刻经的人有寺院僧徒,也有俗家工匠。僧徒从事刻经属于宗教职责,而工匠则是花钱雇佣的。随着采石刻经规模的不断扩大,聚集的工匠越来越多,云居寺渐渐捉襟见肘。另外,除了刻经,皇家宫殿、园林、陵寝等建筑也大量使用汉白玉,从而使汉白玉的开采量日益增大。积年累月的开采使汉白玉产地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坑穴,采石人称之为“大石窝”。因为长期在大石窝工地从事采石作业,工匠们索性在附近定居下来。定居的工匠及其家眷越来越多,渐渐形成了村落,而村名顺理成章地成了“石窝”。
石窝村形成以后,云居寺才逐渐回归佛寺职能。大石窝汉白玉的开采起始于静琬刻经,而在采石刻经的过程中,先后诞生了云居寺和石窝村。自静琬开始,历经隋、唐、辽、金、元、明六个朝代,绵延1039年,镌刻佛经1122部、3572卷、14278块、近3000万字,从而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古老的石刻佛经图书馆。唐开元年间至辽代是刻经活动的鼎盛时期,唐玄宗曾把《开元大藏经》赐给云居寺作为石刻底本,辽代则使用《契丹藏》作为底本。那些凝结着四十余代僧人心血、汗水和智慧的石刻佛经,是愚公移山精神的真实体现。石经的刊刻规模之大,历时之久,在人类文明史上是罕见的。石窝村的汉白玉为这一浩大工程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支撑,那些精美的石头书与石窝村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云居寺的石刻大藏经均刻在石板上,分别藏在九个岩洞内。在石经山半山腰,开凿有九个藏经洞,分上、下两层,其中八个洞为封闭式,装满经板后用石堵门,以铁水浇铸。只有一个规模最大的雷音洞为开放式,静琬最初刻经146块,嵌在洞的四壁。洞内有四根八面的立柱,柱上雕有佛像1056身,故称千佛柱。九个洞内共藏经石4196块。山下寺院内的南塔亦名压经塔,塔下地宫藏经石10082块。全部经石14278块,镌刻有佛经1122部3572卷,堪称世界佛经铭刻之最。为了更好地保护这批珍贵的文化遗产,云居寺于1999年9月9日9时9分9秒将10082块辽、金石经全部回藏到恒温、恒湿、密闭、充满氮气的地宫中。
因为石窝村是由采石工匠聚居而成,而这些工匠来自五湖四海,所以村民的姓氏复杂繁多。现有900多户、2800多人的石窝村,姓氏多达上百个。姓刘的人家相对较多,也不过30户,还不是同一宗族。一千多年来,房山当地人与天南地北的能工巧匠混居在一起,男婚女嫁,繁衍生息,形成了多民族和谐共处的格局。仅明朝永乐年间,出于大规模修建皇城及陵园的需要,就从山东、山西、河北、河南以及南京等地招募了大批工匠,在大石窝从事采石加工等工作。直到清代,仍不断有各地工匠加入进来。这些工匠中的许多人落地生根,成了石窝村村民。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石窝村是一个移民村落。
历史遗迹难寻觅
辽金以后,由于大石窝汉白玉大量用于皇家建筑,不再由僧人主持开采,而是直接由朝廷控制。官府在石窝村设立监督衙门,监督官员往来于衙门与采石工地之间,管理与采石有关的一切事务。明朝永乐年间和正统元年,就有朝廷官员先后奉明成祖和明英宗之命到石窝村督采石料,所采十三陵碑、象、驼、马等石料历时三年才完工。民国时期的《房山县志》还记载了清代修建紫禁城宫殿,派官员督办采石的情况:“清嘉庆六年修复殿工,命侍郎张舜臣、主事李健于大石窝采石。”
当年的石窝村,东西景观大不相同。西边高墙深院,戒备森严,是囚禁犯人的监狱。所谓犯人,就是那些消极怠工或不服从管理的工匠。东边却是店铺林立,一派繁华景象,所以人们把石窝村东口称作东店,那里曾是白带山一带的商品集散地。
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汉白玉开采是在明清时期,成千上万的工匠驻扎在几个营地,以旗语为号令,统一指挥。石窝村西北的青石山就是当年的旗杆山,升旗出营上工,落旗收工回营。石料开采技术性强,难度大。优质汉白玉藏在50米深的地下,厚度一般为0.9米到1.5米,在当时技术条件落后的情况下,仅凭人力用锤子沿石弦破开重达数吨甚至数百吨的汉白玉,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将采到的巨大石料运往50公里以外的京城,甚至更远的十三陵,以及清东陵、西陵,又是一大难题。聪明的石窝人发明了一种旱冰船和链车,使这种运输成为可能。他们每隔一里地凿一眼井,到了寒冬时节,取井水泼地,井水结冰后,再将巨石放置在被称为旱冰船的特制木架上,然后像纤夫拉纤那样以人力拖拉。据说,当年用这种方法将一块长3丈、宽1丈、厚5尺的汉白玉从石窝村运达京城,调用民夫2万人,耗时28天,花费白银11万两。
据考证,当年从石窝村运入京城的汉白玉毛坯料最重的一块达300余吨,这块石料是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运抵京城的,经过雕饰后用在了紫禁城宫殿上。清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重修紫禁城宫殿时,拭去原有纹饰重新雕镂,用于宫殿御路的云龙石阶,这就是著名的保和殿大龙石,又称保和殿大石雕。保和殿大石雕是故宫最大的一件石雕,重新雕饰后,长16.57米、宽3.07米、厚1.7米,重约200吨,镶嵌在保和殿后的御路上,浮雕九条腾飞的巨龙,出没于流云之间,下面为海水江崖,四周雕刻着卷草纹图案,构图严谨,气势磅礴。
当我提出看看村里的历史遗迹时,讲解员浅笑着,无奈地告诉我,已经不存在了。“当年的监督衙门、监狱、店铺,还有运输汉白玉的旱冰船,没有一点痕迹了吗?”我问。“嗯,没有了。”讲解员肯定地回答。“那么,工匠们住的老房子呢?”我不甘心地问。“那些老房子成为危房后,陆续翻新了。现在村里年头最久的房子,也就一百多年。”讲解员老老实实地回答。从旁边走过来的一位村干部和蔼地笑着,证实了讲解员的回答。
石雕技艺传承至今
作为一种珍贵的大理石品种,石窝汉白玉洁白坚硬,石体中泛着淡淡的水印,属于白云岩类奇石。目前,我国的白色大理石主要出产自三大矿区,一是以房山大石窝汉白玉为代表的华北矿区,二是以莱州雪花白、江苏赣榆雪花白为代表的华东矿区,三是以四川宝兴东方白、云南白海棠为代表的西南矿区。由于汉白玉为白色,品质优良,行业内便将上述白色大理石统称为汉白玉。
讲解员看我对汉白玉兴趣浓厚,建议我去看看汉白玉文化艺术宫。“那座白色的建筑所使用的石材,全部是大石窝汉白玉。”她说。然后,又一脸遗憾地告诉我,汉白玉宫已经关闭,游客无法进入,只能看看外观。
从村委会往东百米左右,过马路,就是那座富丽堂皇的汉白玉宫了。一道铁栅栏将汉白玉宫与门前的小广场隔开,铁栅栏锈迹斑斑,这座建筑似乎已经关闭很久。我把手机从铁栅栏的缝隙里伸进去,试图拍下这座建筑的全貌,但因为汉白玉宫坐南朝北,此时刚好逆光。这座建筑的东侧是中华石雕艺术园,由于内部施工,也已关闭。从造型别致的门楼及雕刻精美的门柱,可以想见园内石雕作品的美妙。
马路对面是几家石雕厂,汉白玉栏杆里面的空地上摆放着已经雕刻完成的石狮、石象、石鹰等。一位壮汉从仿古小楼里走出来,笑容可掬地与我搭讪,我们的话题便围绕石雕展开。大石窝汉白玉的雕刻类型繁多,基本的工艺程序是选料、放线、打荒,然后经过挖、打、砍、剁、扁光细作、打磨雕刻等工序完成。在整个雕刻过程中,所使用的工具有锤、錾、剁斧、扁子、墨盒、卡尺、尺板、卡钳、砂石块等。我在大石窝村史馆的展室里看到了这些工具,它们被摆放在玻璃橱柜里,下面铺着蓝色的绒布,看上去似乎很珍贵。尽管这些工具简陋而原始,但到了能工巧匠手上,它们就像被施了魔法,可以成就妙不可言的艺术品。
大石窝石雕工艺兼收并蓄,在消化吸收各种技法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个性鲜明的风格。手艺人的技法传承基本为口传心授,传承关系以父子和师徒为主。在清代以前,手艺和绝活多为家传,儿童自幼耳濡目染,长大成人后,渐渐掌握了雕刻技法,便吃上了石匠这碗饭。后来的师徒传承中,学徒一般从开山学起,接着学习石料加工,然后才能学习精雕细刻。学习周期一般为三年,在此期间,徒弟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决定了学习的效果。

在与石头打交道的过程中,石窝村的匠人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石作习俗。过去,石窝村北街曾有一座鲁班庙,相传修建于明朝永乐年间。该庙坐北朝南,正殿供奉着鲁班塑像。每年农历三月十七,石匠们便聚集在庙里焚香祭拜,因为这一天是鲁班的生日。据说,鲁班有四个徒弟,大徒弟是石匠,二徒弟是木匠,三徒弟是瓦匠,四徒弟是画匠。所以,石匠们将鲁班视为始祖,并将他的生日确定为石匠节。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石窝村的工匠们放假休息,村子里走花会,演出文艺节目,好不热闹。
另一个重要的节日是开山节,在农历十月十五日,相传这一天是山神的生日。开山前祭拜山神是必不可少的一件事,也是石窝村沿袭千年的习俗。采石地点确定后,开山“把头”将墨斗、方尺、尺板这三件主要工具供奉在山前,工具前面摆放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太公在此,诸神退位”。在长期祭拜活动中,那三样工具被赋予了一种神圣色彩,所以不能随便把玩。
采石运石,石匠们以号子为令。号子分为预备号、起动号和停止令。预备号反复唱起时,工匠们进入准备状态。起动号是一叫一答,号手嗓音洪亮,唱起来铿锵有力,工匠们根据节奏,进行起、撬、调头等作业。停止号令为“我撂”。石匠号子朴实而简洁,又不失优美。
独具特色的汉白玉文化使石窝村成为中国民间石作艺术之乡,被誉为京郊走出国门施工第一村。
村后山顶上有块夹杆石,1407年立于此处。古时此处立百尺高杆,上挂青龙旗,定为号令旗,工匠观旗为号,旗升为上工,旗降为下工。
石窝村有个美丽的传说
村前的牌楼。
石窝村村前赫然矗立着一座古色古香的牌楼,牌楼中间是白底红字——京西大石窝。一条笔直的柏油路通向北边的石窝村,村路两边装饰着造型别致的汉白玉栏杆。
正如讲解员和那位村干部所说,村子里已经看不到年代久远的历史遗迹。街边一座废弃的老屋,门窗残缺不全,里面横七竖八地堆满杂物,但临街的背面和侧面新刷了一层灰色涂料,从而遮盖了年深日久的气息。老屋旁边,是一座安装了太阳能装置的新居。与低矮的老屋相比,新居显得宽大豁亮。在离老屋不远的地方,一座陈旧的门楼却安装了崭新的防盗门,灰砖灰瓦与红色的铁门显得有些不协调。作为游人,我注重审美,但作为村民,也许更注重实用。
我在南街游走时,一位面容清癯的老人迎面走来。他看上去弱不禁风,说起话来却声如洪钟。提起这里的汉白玉,他一脸自豪,随口说出许多使用了石窝村汉白玉的建筑,比如,故宫、颐和园、十三陵、曲阜孔庙、承德避暑山庄、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中华世纪坛、人民英雄纪念碑等。“人民英雄纪念碑由1300块花岗岩和汉白玉组成,底座有两层平台,双层汉白玉栏杆,下层有8幅汉白玉浮雕。底部的双层栏杆和所有浮雕所使用的汉白玉石料,全都是当年的石窝石雕生产合作社提供的。”他说这话时,眼睛里闪烁着异样的光彩。
说到石窝村的石匠,老人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明朝永乐年间,石窝村的一个石匠老来得子。因为知道石匠的艰辛,他发誓不让儿子步自己的后尘。夫妇俩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挤出钱来供儿子读书。儿子也很争气,写得一手锦绣文章,书画更是遐迩闻名,成为学堂里的佼佼者。不幸的是,儿子十五岁那年,石匠夫妇相继离世。迫于生计,石匠的儿子不得不继承父业。拉线画样,打碑品石,几年的光景,他已经俨然一个成熟的石匠了。但在工头的眼里,他仍是个派不上大用场的“秀才”。
有一回,工头为了丰厚的利润,接了一个打造“蛟龙碑”的活儿。可他手下的石匠,连蛟龙碑的名字都没听说过,更不要说制作了。工头一筹莫展,但又不肯放弃。因为一旦放弃,不仅丢掉了可观的利润,还会使石窝村石匠的名声受损,外人会把他们看作无能之辈。一向寡言少语的秀才打听到二龙岗有一块蛟龙碑后,找到那块碑,并把它画了下来。然后,他照着自己的画打制了一块精美绝伦的蛟龙碑。工头大为惊奇,从此对他刮目相看。秀才打成蛟龙碑的事传开后,他成了大石窝一带的名人。人们对秀才赞不绝口的同时,也明白了一个道理,他是把学堂上所学的知识与父辈的经验结合起来,才成了最优秀的石匠。可见,只有文化知识能够使石匠这个行当得到提升。
故事讲完后,老人意味深长地笑道,这只是个传说,不一定真有其人其事。但这个传说能够流传下来,表明了人们的一种愿望。
(原标题:汉白玉孕育了石窝村)
来源 北京晚报
流程编辑 TF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