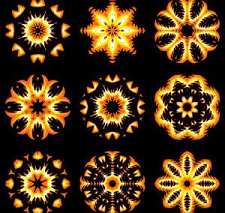启功先生的佛缘与境界
发布时间:2024-10-25 04:04:17作者:佛心网
启功先生的佛缘与境界
作者:李山
来源:《中国宗教》2006年第8期
启功先生,字元白,1912年生于北京,满族。幼年丧父且家境中落,自北京汇文中学中途辍学后,发奋自学。后从贾尔鲁先生(羲民)、吴熙曾先生(镜汀)习书法丹青,从戴绥之先生(姜福)修古典文学。刻苦钻研,终至学业有成。1933年经傅沅叔(增湘)先生推介,受业于陈援庵先生(垣),获闻学术流别与考证之学。
援庵先生慧眼识才,聘为辅仁中学国文教员;1935年任辅仁大学美术系助教;1938年后任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兼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从事故宫文献馆审稿及文物鉴定工作;1949年任辅仁大学国文系副教授兼北京大学博物馆系副教授;1952年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
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启功先生是当代著名学者、画家和书法家。他著作丰富,通晓语言文字学,作得一手好诗词,同时又是古书画鉴定家,尤精碑帖之学。2005年6月30日凌晨,启功先生因病逝世,享年93岁。
为了纪念启功先生,他的学生李山教授撰写了这篇回忆文章。
记得有一次笔者帮启先生填表,其中有一栏是“宗教信仰”,问先生怎么填,先生说:“填上吧,佛教。”熟悉启先生的人都知道,先生经常会谈到佛教,当然也谈到基督教或其他宗教,但还是佛教方面多。有一次参加博士论文答辩会,先生感冒了,有点咳嗽,先生慢悠悠地打趣说:“有位龙祥和尚,感冒了,咳嗽。龙祥就说:维摩病了,说法不已;龙祥病了,咳嗽不已。”引得在场者哈哈大笑。启先生的心灵,永远是这样的活泼!
像这样谈佛教的趣事很多,不过,就笔者所知,先生几乎从未说过“我信仰佛教”之类的话,所以填表时需要问一问。人们感受到先生对佛的敬重,是从他对佛理的妙谈,对佛教掌故的博雅获得的。启先生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和乐平易的境界,用“老禅和子”一语形容,也许最恰当。
启功与佛教的缘分很深。3岁时,失去父亲的启先生就被家里送到雍和宫,做了一名记名的小喇嘛,后来还接受过九世班禅大师的灌顶。在雍和宫做佛弟子的经历,平日里先生曾零星地说起过。到先生去世前不久,作《启功口述历史》时,才对这段事有比较详细的交代。
先生在雍和宫的师父叫白普仁,师父给他起的法号是“察格多尔札布”,意思是佛祖保佑。在雍和宫里,先生学佛经,念《大悲咒》。这段“出家”的日子,留给先生很深的印象。启先生对宗教,具体说对佛教,还有一个“往大里说”的态度。在《口述历史》中,说到白师父对他的影响时,先生说:“我从佛教和我师父那里,学到了人应当以慈悲为怀,悲天悯人,关切众生;以博爱为怀,与人为善,宽宏大度;以超脱为怀,面对现实,脱离苦难。”
在同一段文字中,启先生还讲到了他的“小喇嘛”生活带给他的宗教体验。20岁时曾祖母生病,深夜中他一个人到雍和宫去向“喇嘛爷”求药,本来很害怕,但一见到庄严的庙宇,一座一座在清风明月下矗立,忽然想起《西厢记》中“梵王宫殿月轮高,碧琉璃瑞烟笼罩”的唱词,“眼前的景色,周围的世界,确实如此,既庄严神秘,又温馨清爽,人间是值得赞美的,生活应该更加珍惜。我心里不但一点不害怕,而且充满了禅悟后难以名状的愉悦感,这种感觉只有产生于对宗教的体验。”
《启功口述历史》实在是一份“抢救”的文献,因为在它完成不久,先生就病重了。整理者记录下这样一份文献,实在是叫人大感念的事。而且,上面的文字中说到的“慈悲”、“博爱”、“超脱”,都是先生为人的实况,千真万确。不同的是,启先生平日表现出的境界,是“扫平”了的,是“不着迹”的。
某家报纸多年前曾报道:启功不打假。有意思的是启先生还到卖假字的地方去看,据说有位卖字的老太太还说:“这老头儿好,不捣乱!”先生去世后,灵堂里有一位跪在先生灵位前磕头的,经探问得知就是做那一行的。笔者也曾就“不打假”的事问过先生,先生说:“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鄙事。像我年轻的时候,学写字,学画画,不过是想有点挣钱的本事,养活我的老母亲。这些人弄几张假字,卖几个钱,也是谋生。何苦跟他们过不去啊!”这是慈悲,也是博爱。启先生表现出的“宽宏大度”,更像一个平民对更多平民的体谅。可是,慈悲也好、博爱也罢,若无这点“体谅”之心,又如何可以呢!
不过,在先生说到“假字”现象时,就是连“吾少也贱”那样的话也不愿多说的,他更愿意在这样的事情上“开哄”——一个先生常说的字眼儿——说有些假字写得“比我好”,是“伪而不劣”,而自己的字是“不伪而劣”,还说能写出逼真假字的都是朋友等等。这便是先生的幽默和宽容。真性情而出之以幽默或曰“开哄”,或者说一位好心人外加气韵生动的“淘气”(也是先生常说自己的词),才是完整的叫人难忘的启先生。
体谅是真性情,可以学,因为德行本身有榜样的价值。但先生的“淘气”,却是大才情的余裕,一般就只有体味的份了。早年启先生的一位老友说过这样的话:小启这人你拿他没办法,什么事在他那儿,都是说“狗屁”。晚年先生回忆起老友,想到他说的话,说:“我现在不‘狗屁’了,我现在是‘狗而且屁’。”
先生的名气大,听到的恭维自然少不了。一次先生忽然对恭维他的人说:“我是神。”接着又说:“我什么神?我是‘牛鬼蛇——神’。”一位北师大文学院与先生同事多年的老师说,启先生的高明,是他不论写文章,还是与人谈学问,总先说“我不懂,我是胡说”。
北师大文学院开会讨论启先生的学问,等到会议结束时,启先生发言。这时的发言最不易,也最易落俗套,但启先生起来,先说:“过去,有一回邻居家的小朋友来我这边玩,怕他们闹,就说你们乖,你们玩去吧。”说到这里,听众不明就里。接着启先生说:“那两个小朋友真有意思,他们一边走,还一边问:‘我们怎么乖了,他就说咱们乖?’”接着归入正题,“今天的会议,我就像那邻居家的小朋友,我哪儿乖了?大家这样捧我?”
人们可以从中华书局办的《学林漫录》中,看到启先生早些时候写的“自讼”文章,反驳自己先前的说法,到晚年还是那样勇于认错。早年写过关于《千字文》的文章,晚年发现自己对周兴嗣“次韵”的说法理解错了,不顾年老体衰,还是写文章纠正自己。当时,与先生说起这事,笔者还听到先生骂自己“糊涂”。
佛家讲究破我执,舍贪著。笔者师从先生十余年,敢说先生最无“我执”。常拿自己“开哄”,是无我执。手写的书稿让人借走了,那位朋友又转手卖商人,多年后又流回内地,启先生不但不生气,把它买下来,还打趣地题了诗。说到这件事,启先生淡然地说:“他那时需要钱。”
笔者还知道这样一件事:一笔给人写字的酬劳钱,被一位朋友“中饱”了去。事发了,他说是给先生买书了,可书一本也未到先生手。别人很生气,先生只是呵呵一笑:“嗨!他这人没出息你又不是不知道。”与这位朋友,以后该怎样还怎样。启先生对此事的“处置”,那份淡然无执,笔者的感受太深了,现在写起来文字没法将那份从语气、表情中透出的淡然表达出来!
写到这里,我想起佛教、基督教及其他宗教都会讲到的那个“德福一致”的问题。这问题放在西方哲学里讨论就难了,因为他们强调一种客观的境地,以为在客观上强调应有一个可以使“德”与“福”统一起来的实际境地。
笔者以为,像先生那样什么事都可以“狗而且屁”,不生气、不计较——不是有气忍住不生,心里计较装作不计较,而是真超脱——就是德福一致。生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可以给人带来伤害,想从客观上改变这事情,比上天还难,但是心地宽阔就不同,宽阔一分便得一分自在,便增一分境界。禅门老话为“不湿脚”下的“转语”是“脚不湿”,前者强调客观,后者则从主观一面下手,启先生的“脚不湿”就来自他的心境宽阔。
启先生似乎从来不长篇大论地讨论佛教问题,他喜欢在他那“淘气”的诗篇里说禅说佛。启先生虽然是黄教的佛弟子,但与他的诗篇一样,平时讲得多的还是禅宗故事。记得先生曾说,看《灯录》、《五灯会元》不一定好,那上面神化的内容太多,要看,看《景德传灯录》,看《祖堂集》;还说,你看《祖堂集》里记六祖的事和《五灯会元》差多少啊。先生还说过印顺和尚的《中国禅宗史》写得不错,平实。吕秋逸先生的佛学著作也好,说有一次生病时住在医院里,几大本全看了。
喜爱佛家,当然是喜爱佛教拿得起放得下的大境界。先生在《布书袋铭》里说:“手提布袋,总是障碍,有书无书,放下为快。”“放下为快”正是启先生喜爱并且是可以“自况”的境界。但这些诗篇与“贩禅”的不同。请看这首《沁园春·戏题时贤画达摩像六段》:
片苇东航,只履西归,教外之传。要本心直指,不凭文字,一衣一钵,面壁多年。敬问嘉宾,有何贵干,枯坐居然叫做禅。谁知道,竟一花五叶,法统蝉联。断肢二祖心虔。又行者逃生命缕悬。忆菩提非树,那桩公案,触而且背,早落言诠。临济开宗,逢人便打,寂静如何变野蛮。空留下,装腔作势,各相俱全。
这首词,从禅宗老祖,到一花五叶,下及“曹一角、临天下”临济宗的禅门历史,全说到了,也几乎全批评到了。如果说“敬问嘉宾”几句,是跟达摩面壁“淘气”,那么,对二祖以后特别是临济宗以下的教史,就是批评了。
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神秀、慧能那两首著名偈子的理解。在这首词的末尾,作者还加了一个小注,说:“秀、能二偈,分观各有精义,合读则如市人口角,一曰即是,一曰即非,浅直触背,不知何故。”这可是在翻一件禅门大案!因为据《灯录》记载,慧能的偈子是得到五祖弘忍认可,并以此获得法衣的。可是在启先生看来,神秀的偈子同有其精义。
以笔者浅陋的理解,道理在于慧能的偈语是从境界上说,而神秀则从修行上说。“明心见性”了自可说“菩提本无树”,可若没有基本的修行,光是讲“顿悟”就能达到“非台”、“无树”的境地吗?

对禅门中“棒喝”,启先生是不赞成的。先生另有一首诗涉及“棒喝”事,说:“德山棒其徒,南泉斩其猫。既秉具足戒,杀气何其高。”(《少林寺一千五百年征题》)说棒打、斩猫是破戒行为。对这些公案,历来不乏参解。笔者记得启先生曾经说过,这样的事情,未必从佛家教义上理解,“棒喝”尤其“斩猫”之类的出奇之事,实际是和尚“树立权威”的举动。
这样观点,写成文字,一定要引起波澜的,或许正因如此,先生宁愿在诗里表达。诗嘛,兴到之语,会心的一笑,不会心的一愣,也就过去了。自家吃饭自家饱,佛家的义理,本是一个心路上的事情,写文章讨论,反而落言诠,若再起争执,就更不好了。
在启先生的诗集里,还有一首是写弘一大师的。常到启先生家的人一定知道,坚净居二层房间靠门的墙上挂着的那张弘一大师的像,还有正面墙上弘一法师写的“南无阿弥陀佛”的横幅。挂像的旁边有丰子恺先生的笔迹,那张像就是丰子恺先生送的。说到弘一大师和丰子恺先生,先生是钦佩、称赞有加,先生家里就有全本的《护生画集》,还以“真高明”称赞丰先生那幅名为《我的腿》的“护生画”。先生还称赞弘一大师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地”。
启先生在专写弘一大师的诗中称赞大师的“独行”,称赞大师的书法和佛教修为,说他是“并世论英雄,谁堪踵其武”。可是,这首诗在写到弘一大师的出家时,却说:“稍微著形迹,披缁为僧侣。”弘一大师出家入的是南山律宗,持戒极严,启先生说多次与人谈到弘一的持戒。弘一大师出身进士、盐商富贵之家,早年在文艺界是著名的大才子,看破了红尘决意出家,在佛教“烂熟”的时代里,就有意皈依了律宗。所以如此,启先生曾说,那是因为他有很强的救世之心,既然救不了世界,就自己跟着吃苦。说他“稍微著形迹”也是指他这点而言。
谈到启先生说禅佛的诗,自然会想到他生病住院的诗篇。从上个世纪的70年代起,先生年高多病,用先生自己的话说是身体“折旧”。先是有美尼尔氏综合症,后来又有骨质增生,再后来是心脏又不好。不管是住院治疗,还是在家里做牵引治疗、养病,先生都写了不少诗篇。
如写美尼尔症就有三首《沁园春》。请看其中《沁园春·美尼尔氏综合症》中如下的句子:旧病重来,依样葫芦,地覆天翻。怪非观珍宝,眼球震颤,未逢国色,魂魄拘挛。郑重要求,“病魔足下,可否虚衷听一言?亲爱的,你何时与我,永断牵缠?”
人生病都想病魔赶紧离身,先生自不例外。可是像他这样子称“病魔足下”,称“病魔足下”为“亲爱的”,这等的言语,可不是谁都道得出来的。病中还有一个不病的,这“不病的”,就是启先生的幽默。
另外还有写颈部牵引的《颈部牵引》篇。诗由颈部牵引,想到北京西郊动物园的长颈鹿,又由长颈鹿的长颈,想到东汉著名的“强项令”董宣。然后思路一跳,又想到与孔子相关的“西狩获麟”的传说,说有的考证家认为“西狩”所“获”之麟,就是长颈鹿,孔子称之为“麟”是“多怪由少见”。然后说到自己颈部的骨质增生,开玩笑地说自己“增生”的长度是向长颈鹿看齐的。但“颈牵一丈长,腿仍二尺半”,牵引到最后,还是一个“且作麒麟楦”。
病痛煎熬之下,依然妙笔生花,心意灵转,可称是以“法眼”观病,其中的幽默诙谐,其中的“淘气”,真是修炼得“金刚不坏”一般了!
摆脱世间烦恼,佛家修炼有所谓不净观、白骨观等法门。看启先生的诗篇,也有一种“观法”,我们就姑且称之为“烤鸭观”吧。诗集里有一首《贺新郎·烤鸭》,“烤鸭”比喻人在火炉里的情形。词的下半阙这样写道:
三分气在千般好。也无非,装腔作势,舌能手巧。包上包装分品种,各式长衣短袄。并未把,旁人嚇倒。试向浴池边上瞧,现原形,爬出才能跑。个个是,炉中宝。
在一些写启先生人生境界的文章里,常看到一些说启先生“看透了”之类的话。不错,以启功先生的大智度,当然是看得很透。但“看透了”绝难说是启先生的生活意态。就像这首诗,不作白骨观,也不作不净观,而是“向浴池边上看”,向“烤炉”中看。若作白骨观等,那是要脱离这个世界,但作“烤鸭观”则不然,毋宁说是讽劝“人间世”的人们,以“放明白点”的意态去对待生活。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启先生是得了中国佛学的精神的。
佛教义理在中土的发展,不就体现在“不悟道劈柴担水,悟道还劈柴担水”之类的语句所显示的将“出世”与“入世”打并为一的精神吗?因此,先生晚年在说到从雍和宫庄严佛地获得的彻悟中,有“人间是值得赞美的,生活应该更加珍惜”之言;也因此,他无限地眷顾在天上的老师、夫人,称那些曾对他有帮助的人为“恩人”;也因此,他以古道热肠的心意,捐助失学的儿童,以平等的心态体谅生活艰辛的普通人。
“看透了”的启先生绝不“独坐孤峰顶”,而是在返回生活的“随波逐流”中,“不着迹”地将其对生活的珍爱,展现为大智的幽默和乐观。因此,他也为红尘滚滚中的世人,树立起一种平常而又大境界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