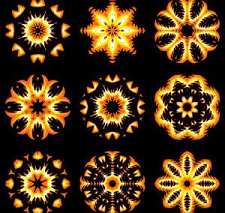和中国版不同,《浪矢解忧杂货店》突出了原著中的日本生死观
发布时间:2024-10-16 04:01:51作者:佛心网
和中国版不同,《浪矢解忧杂货店》突出了原著中的日本生死观
在广木隆一导演的电影《浪矢解忧杂货店》中,主人公浪矢雄治爷爷在杂货店的最后一晚,皆月晓子以年轻女子的形象陪伴在他身边,一起品评那些来自未来的信件。皆月晓子是浪矢爷爷的同代人,年轻时与他相爱,后私奔未果而分道扬镳。她本来已经暮年离世,为何她的灵魂能复现在浪矢爷爷的杂货店中?皆月晓子的灵魂复现这个情节是东野圭吾原著小说中不曾有过的,在韩杰导演的中国版《解忧杂货店》中更是未有出现。在前文《相比东野圭吾原著,电影 解忧杂货店 忽略了社会经济背景》中,笔者从社会现实的角度,解读了《解忧杂货店》中失落者和得意者、乃至死者和生者之间的关系。而本文作为相应的姊妹篇,则要从奇幻观念的角度,结合广木隆一版《浪矢解忧杂货店》匠心独到的改编,阐释《解忧杂货店》中另一条重要线索:即浪矢雄治和皆月晓子、杂货店和孤儿院“丸光园”之间的“线”,与孤儿们人生命运的超验联系——这种超验联系根植于日本传统文化的生死观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