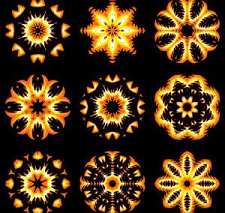吕建福教授:实践与解说——吕建福先生佛学笔谈录
发布时间:2024-10-10 04:05:26作者:佛心网实践与解说——吕建福先生佛学笔谈录
问:年前南京“金陵刻经处”出版过一本名为《闻思》的纪念文集,先生曾发表了一篇专题论文,关涉的课题是在近代中国佛教思想方面;此外,也在北京的《法音》以及《佛学研究》等刊,续有许多篇佛学理论的文章问世。您的学术研究工作着实於佛教方面,当然跟个人的求学宗趣及学思历程有关。这里,请先生详述一下好吗?
答:1997年金陵刻经处创办《闻思》,本拟为大型佛学丛刊,相当于“佛教思想文化评论”这样的刊物,后因种种因缘,成了一本纪念文集,颇为遗憾。但其中还是多少体现了一些我创刊组稿时的构想,即是佛教界的自我反思和自身建设亟待思想文化的评论,而学术界的佛学研究也应在传统的佛教史、人物、宗派、经典等的研究外,更多地关注佛教界的现状和佛教的未来。同时,佛教自身也应以其内涵的佛法智慧去观照时代社会乃至世界人类文化,面向现代、关怀社会、融汇文化,这可能也是当代佛教生命力之所在。这两者都需要有学术研究的倡导和思想文化的评论。在四年后的今天来看,这样一份《佛教思想文化评论》似乎仍是佛教界和佛教学术界所需要的。说到个人的学与思,基本也在这个方面。佛学的研究,最重要者是要体会释迦牟尼佛的本怀,识得佛法的根本价值和广大机用,学以致用,既用以个人生命境界的提升,也用于社会文化境界的提升,即佛法所说的自利利人。
问:佛教侧重出世的思想,这是历来的讲法。然而,近世中国佛教的发展,自杨仁山为首的居士学团,或者太虚大师领导的僧伽团体,似乎很明确地揭示“体验之学”的格局而为说。所谓“体验之学”,是一种真实的生活实践,通过生活及人生的体验,而给予真切的关怀,从而抉发宗教生命的精神价值。这种情况,於晚清以来,尤见明显。但此说有时贤认为,杨仁山、太虚等人的终极信念,除了彰显固有的价值依向外,还要对当时现实的情境,给予积极的关怀,这有所谓通过宗教的信念与实践,来净化人生、教化人生。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的目的,当可如此解说。考察近世中国佛教的活动,实有其特色,除了上述由“体验之学”的理念来解说外,先生认为还可以着实哪些层面来看呢?佛教的修行,不但是一种真实的实践,且也是一种“参悟”的意念。这个见解,您认为如何呢?
答:以“体验之学”来阐释杨仁山居士、太虚大师的佛教理念和事业,也不失为一种方便之说。就佛法来看,佛法从来就是“体验”的,用佛教自身的语言来说,是“解行并重”的,是需要“修行”,需要“体悟”或“体证”的。而这种“修行”,就在吾人的身口意“三业”上修、就在人的日常生活、语默动静中修。传统所谓“出世”,从现象上似乎离群索居、剃发出家、山林坐禅便是“出世”了,实则只是修行的一种方法或一个阶段而已。若其寺院或林岩修行,乃为培植道力更有力量来入人群、自度度人,则现象上的“出世”即是本质上的“入世”也。近今所谓“入世”,从现象上不离人群、即在社会人群中修己利人,似乎便是“入世”了,实则其目标仍在终极解脱并度人“解脱”,则也不异“出世”也。只是由于传统王权(世俗政治)的力量,使佛教较难实现“入世”的功能(尤其是明清以后),积非成是,大家便以为佛教是“出世”的,而近代以来杨仁山居士之关怀现实社会、太虚大师之倡导“人生佛教”似乎是新鲜事(当时于佛学深有研究的梁漱溟先生即如此认为),才是“入世”的了。就佛法来看,世出世法是圆融的,只是不同历史时期,因不同的社会机宜而有不同的现象而已。就近现代来看,佛教之关怀社会,在现实人生中修行、倡导“人间佛教”,是既合乎时代因缘,也是切合释迦牟尼佛的本怀的,应该是佛法的本来。“参悟”是佛教修行的一种方法,是“真实的实践”的一个内容,主要着重在悟明心性,但绝非“参悟”之后便即到家,尚有“悟后起修”之广大行。“悟”前的种种修行(广积资粮种种加行)及“悟”后的积功累德,五十五位真菩提路直至圆满成佛,均是佛教的真实实践。
问:佛教法义的实践性,或许会指涉到内在及超越的认知层面上。准此,吾人对现实人生的证行问题,便会在这种层面上而为说。有教内中人认为,安立佛教的“儒学化”,正好把它的实践性抉发出来,对现实人生的证行,是有所依向的。这个讲法,考析其底蕴,当可以取决於认知的理念而为说。佛教的“儒学化”理念,固然会指涉到内在及超越的认知层面,先生可否就时代思潮的背景,给予阐析一下好吗?
答:诚如您所说,有许多讲法需“考析其底蕴”、“取决于认知的理念而为说”。佛教“儒学化”问题,就我所知,在佛教界内影响是很小的,在学术界确是有人在研究、在努力。如民国时期的一些佛教学者如熊十力、梁漱溟等,其本身的学术历程某种程度上即体现了这一点。后来新儒家倡导者也有这方面的思想。若论其时代思潮背景,当出于对传统佛教的不满,即传统佛教到清末民初已相当衰朽,离佛教应有的社会功能相去极远。一般民众对佛教的理解也基本倾向于祈福求B073和死后及鬼神,当时即已为太虚法师痛心疾首、激烈批评。相对而言,儒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明确而富有朝气,虽南宋以后儒学为封建王权所用几乎成为“孔家店”,因而在“五·四”时期受到大冲击,但有识之士始终明白儒学千古不易的伟大精神和实践价值,中国知识分子也一直从中得到精神滋养。提倡佛教“儒学化”,当是出于佛教于现实人间缺少关怀的现实,希望以儒学的人间实践性以济佛教之不足。这可能就是您说的有人认为“安立佛教的‘儒学化’,正好把它的实践性抉发出来,对现实人生的证行是有所依向的”。
愿望固善,但于佛法之知见是有偏差的。因为佛教涉入现实社会较少,是长期封建社会王权统治所造成的格局,并非作为佛教之内涵的佛法义理所固有。佛教法义的实践性,有世间法,有出世法,并且是即世间法而出世,而出世法亦不离世间,这就是世出世法的圆融性,如《六祖坛经》中所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绝不只是“指涉到内在及超越的认知层面上。”若言“内在及超越的认知层面”,儒家亦有其“心性之学”,且为儒学实践的根本修养,后儒如陆九渊、王阳明等大力倡导,实则源自先秦,孔孟、荀子等大儒即以此为个人修养根本。此“内圣”修养相当于佛法的“证体”功夫,而治国、平天下之“外王”,则相当于佛法之“启用”也。只是历史文化的原因,儒学定局为治世,而佛教则“山林化”,偏向于“治心”了。从学理上说,佛法之心性学较之儒学更为系统精深,而从实践上看,千余年来,则儒学于现实人间确实涉入更多。这是历史的因缘,非佛法之本来。若于太虚、印顺等法师所发掘、倡导的“人间佛教”思想有具体的了解,于此当能无惑。
问:宗教的终极价值,自有其实质的意义。佛教在这面似乎别具一番深意,最明显乃是“生与死”这个问题。说“生与死”,也属老生常谈之言。如何通过理念来体会它的终极价值?这当然要有相关的工夫和信念,您认为此说对吗?佛教每每着实虚妄的理念而为说,依此,它的终极价值与这种理念,便会有密切的关系。有人认为,佛教在这方面所彰显理境,就实质的型态来看,是有它的作用而为说的。这个意思,您认为怎样呢?
答:宗教发源于人性深处,故其价值是永恒的。只要人性中的这些问题没有解决,用现代西方哲学的术语,只要人的这些“存在性”问题未得解决,宗教是永远需要的,并且在这方面对于人生的价值,远远超过了科学和哲学。透视人性、透视人的生存境况愈深,便愈能领会宗教的必要性以及宗教价值的伟大。譬如“生死”问题,凡蠢动含灵莫不有“生”也莫不有“死”,而唯有“有意识的人类”能反思及此,思考个体生命及整体人类的生来死去问题,这是人类独有的生存处境,不同于无反省意识之动物之虽死而不知有死。人类文化建立于人的有意识的反思,其中有服务于物质性生存需要的物质文化,也有服务于精神性需求的精神文化。宗教则是人类精神文化之花,对人类所创造的伟大的物质文化也起着关键的作用,汤因比因此谓“宗教乃文明生机之根源”。故宗教的终极价值是无论如何高喻之也不为过的,这一点纵观人类文明史应可知晓。就个体生命而言,“生死”确是一个根本的“存在性问题”。佛教的“生死”学说,具体来说为“十二因缘”说,广义来说,凡“四谛”、“八正道”等,无不为佛教的“生死”学说,不仅揭示了“死”往何处去的问题,也说明了“生”从何处来,并指出其根株在“无明”,解决生死问题之关键则在破“无明”而生“智慧”。无论“无明”还是“智慧”皆生于“心”,故人之“心”乃生死问题的中枢。若以“生死问题”而切入佛教,如您所说的“通过理念来体会它的终极价值”,确为正途,即佛教常说的因“生死事大”而发心学佛。这基本还是一个知见问题(“解”的问题),而不是“信念”问题。真正解决生死问题则需要修行,是需要您所说的“工夫”的。佛教在这方面所彰显的道理,由于源自觉悟自心的智慧而非仰赖外力(如神灵)救度的信仰,对于关注生死问题的人们应该说是最具价值、最值得重视的。
问:考析佛教唯识哲学的基本观点,依世亲菩萨《唯识三十颂》这文献里,当可以得到理解与体会。“我”与“法”的存在,从唯识宗的角度来看,皆涉及意识的转变而为之。准此,有学人认为,唯识宗的识转变对建构我们的言说世界,是含有循环相生的意义。这个讲法,即是指出:一切唯识的认知活动,皆由意识的转变而衍生出来。对言说世界及言说性结构的作用来说,上述理论是不是确切呢?先生在此可否援引唯识宗的某些论典予以解说一下呢?
答:佛教唯识学就佛法本身来说不是一种哲学,而是一种观修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其建立学说、分辨法相,最后目的乃在瑜伽行中破相证性、转识成智,与佛教其他各宗同一归趣,只是方法路径有所不同。由于唯识学建立体系、分辨诸法性相相当精细,相应于人类的意识世界犹如一种精深的哲学,当作一种“哲学”来研究也有确立佛法正见的作用。我于唯识学只是初学,谨就您所提诸问,尝试共同探讨一下。

问:探讨人生解脱的课题,依瑜伽行派唯识宗的观点便认为,人生要解脱必须由熏习作用的层面而为之。依此,所谓“正闻熏习,如理作意”,便成为实践与体会的向度。然而,有学人指出,唯识宗抉发熏习的功能,是把意识理解为超越的体性,而有所依持的一种经验性格。但这种经验性格,并不能有效地展现实践的作用。这个意思,先生认为如何呢?再者,也有学人提出这样的见解,玄奘、窥基把印度佛学的唯识理论,给予超越的理解,这可能都不是原来的意思。您对此有何解说呢?
答:佛法修行的根本次第不离“闻思修证”,“闻”与“思”广义地说均是修行,不只唯识宗之“正闻熏习”、“如理作意”,佛教各宗之“闻思”均乃修行,如您所说的“成为实践与体会的向度”。唯识宗之特胜处在于将“熏习”的道理说得深细而透彻,有能熏四义、所熏四义,在七转识与第八阿赖耶识因果相续的道理上说明“熏习”的修行原理。您所说有的学人的见解,吾未闻其详。意识如何成为“超越的体性”?又如何不能“展现实践的作用”?熏习与修行的关系,除了唯识宗外,其他经论也有阐述,如《大乘起信论》分析了四种熏习、《菩提道次第广论》强调听闻正法及思维观察修之重要等。奘基学是否合于印度佛学的唯识理论,当然可以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来进行研究。但以我个人的浅见,与其研究这样一个问题,不如来研究唯识学关于宇宙生命的本义。就印度佛学的唯识学而言,其各大论师也有见解上的差异,以何为准?玄奘大师当时在印度学冠群雄、论辩法义、折服五印大小乘人,诚乃“千古一人”,其成就得到公认。近世以来,疑古之风甚行,乃至怀疑奘基之学也成为所谓“中国化佛学”、不是印度原来的意思,吾不知其可也。
问:大乘佛教的实践观,着实菩提心的展现而为之。这个理论,固然指涉到清净的、F546在的法义精神上。说大乘佛教的心性论,是一种“一性皆成”的思想,此说可否确切吗?若如此,则所谓大乘佛教心性本净的理论,它彰显的内涵是着实哪方面呢?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内在义、实质义,是否置於心性本净的理论上,便可以提供必然的基础吗?请先生详析一下。
答:以我对于佛法的理解,大、小乘之别的关键在于行愿的大小,而不在其“心性论”方面,正如您所说“大乘佛教的实践观,着实菩提心的展现而为之。”若就“心性论”(一般哲学之“本体论”)而言,小乘佛教之“三法印”与大乘佛教之“一实相印”(“心印”)完全是统一的,可谓一脉相承、同是一缘起法则的展现,若言差异,只是开合不同而已。大乘佛教的“心性论”,也即大乘佛教的“实相论”,心性即是实相——宇宙生命的究竟真实。若论其相,可谓无相无不相;若论其性,可谓空而不空;若论其体,超言绝虑、非有非无;若论其用,宇宙生命之万事万物(万法)无非心性的显现、无非一实相也。若说是“一性皆成”固然可以,然此“性”需从无相无不相、空而不空、超言绝虑、非有非无去体会才不会落入一般哲学追索形而上之“本体”的窠臼。“心性本净”乃是从成佛依据上说的,其“净”乃究竟之净,若对“染”而言,则如《心经》所说“无垢无净”。“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说应该根置于大乘佛教的一实相印(也谓“心印”)才成为“必然”,而不是“心性本净”说。东晋高僧释道生在《涅B231经》译出之前即反对一阐提无佛性说而提倡“一阐提人皆得成佛”,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正是根据《法华经疏》上“万法虽异,一如是同”(大乘一实相印)而得出的。
问:中国佛教学术的研究问题,有人觉得应当切实地扣紧体验与修持。做为佛学研究的时代学人,如何把握法义而为体验与修持的准则?这实在是很重要的,您的见解,是否依向於法义的确切了知而为说呢?如何理解修学的内涵与次第?这也是很重要的,先生的经验,又是否依向於法义的理念而为之呢?
答: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多年来在国内佛教学术会议上经常有人提出,表面上似乎构成了“教界”与“学界”对佛教学术研究态度的不同。强调佛教学术研究需有“体验与修持”的基础,往往是“教界”的看法,“学界”则将之归入“信仰”一边,以为是信仰上的问题,对之既等尊重又慎重,不愿深谈。实质上,无论教界、学界,关于佛教学术研究的基础问题,本身应该可以作为一个共通的问题来研究,这样有利于教界、学界的真正沟通和佛学研究的深入,回避不是办法,应该说也不是真正的“尊重”。学术研究以客观求真为基本态度,佛法也以“如实观”为根本精神,本来并无深入探讨的必然障碍。在我看来,通常将佛教界重视佛学研究需有“体验与修持”的基础归为“信仰问题”,这在学术上是并不正确的,也是没有明了真正的佛教精神的。而佛教界有些人强调佛学研究需有“修持”,若带着“信仰”的情见,以为不信佛便不能进行佛学研究,同样也是不明了佛法的真精神的。我常以为,一个人开始不信佛法,而研究佛学,倘若真以客观求真的态度去研究,久之将为佛教教理的博大精深所折服,愈来愈明了佛法关于宇宙生命的正确道理,渐渐会亲近乃至相信佛法的,这就是“文字般若”的力量。由“见”而“信”才是“智信”,在原始佛教里,“信”的内涵就是“见”。倘若研究佛法多年而不起信,以佛法的立场来看,应该说是尚未真正明了“佛法”的缘故。此外就佛学研究而言,也有领域的不同,除“法义”的研究外(传统之“义学”研究),还有佛教历史、人物、宗派、经典翻译等方方面面的研究,以通常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如语言学、文献学、社会学、史学等)对厘清佛教的某些史实、疏理佛教发展的脉络、辨析佛教与社会的关系等,往往能得到极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应引起佛教界的重视,可为佛教自身建设、佛教事业发展之重要参考。至于“法义”的研究,即作为佛教内涵的“佛法”关于宇宙和生命究竟说了什么,以及提供了怎样的方法去明了宇宙生命的真实,这方面的研究,无疑是需要有“体验和修持”的基础的,以通常的哲学、文献学、宗教学等学术方法来研究,是很难中其肯綮的。即如儒家学问之研究,离了体验,也很难把握其精义,何况发自人性对宇宙生命之深层悟证经验的“佛法”呢!当年熊十力与冯友兰先生论儒家之“良知”,冯友兰将其作为一个学理“概念”来探讨,即遭熊十力呵斥,因为在熊十力的“体验”中,“良知”是人生一个真真实实的“经验”。佛法之“般若”、“空性”、“观照”等概念和方法以及禅宗研究中之公案禅理,倘无一定的体验和修持而作纯学术的所谓“客观”研究,大多是隔靴搔痒,得出的结论往往似是而非,这在学者本人却是不自知的。当“积非成是”以后形成了所谓的“学术研究传统”,对真正的佛法研究就构成了障碍,这在佛学界是屡见不鲜的。即使就通常学术研究而言,当研究到“宗教”,若不重视宗教的“经验基础”,不去尝试对“宗教经验”哪怕作“比量”的了知,恐怕也很难说是客观求真的学术研究。所以我认为将教界注重佛学研究之“体验与修持”归为“信仰”问题是不确的。我的见解,不敢说已经是“依向于法义的确切了知而为说”,但力图去“确切了知”佛法的真实义,确是我研习佛学的愿望和取向。至于“修学的内涵和次第”,如前所述,“闻、思、修、证”是研习佛学的根本次第;修学的内涵,则以超越庸常人生而希求解脱,帮助他人觉悟宇宙生命的真相以及着实体悟缘起性空的法义为三个主要方面,这就是《菩提道次第》等经论中抉发的整体佛法的三个根本要义:解脱心、菩提心和空性正见。
问:宗教义理的会通课题,已经在国内外表述不少。要会通自然涉及意识、理念及方法等问题,怎样取得切当与理想?这是值得关注的。先生认为宗教义理的会通,除了方法之外,尚须要哪些条件呢?儒佛二家的义理精神,当有会通的面向,这是欧阳竟无大师由所强调的,您觉得他的论点是否全面、具体?
答:宗教义理的会通,不仅是宗教学研究的课题,也是人类文化发展到现时代的一大课题。享廷顿“文明冲实”说虽有偏弊之处,但在指出未来世界人类文化中不同文明的差异将给全人类带来越大的影响这一点上,是卓有远见的。人类进入21世纪,社会信息化、文化全球化乃时代之大因缘。在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时代,东西方文明及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比较和会通,将比人类以往几千年历史的任何时期都显得重要和迫切。宗教在人类文化系统中居于极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是文化的精神之源,对文化深层的宇宙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影响极大。有人甚至认为文化对话的关键即在于宗教对话。但宗教的比较会通颇不容易,如您所说的“意识、理念及方法等问题”极为重要。就意识和理念而言,如上所述,在今天应具有全球化时代的意识和减少文明冲突,有助于建设世界人类一体多元文化的理念,促进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至于方法,依佛法而言,可以说是“法无定法”,只要有益于不同宗教的沟通、能增进各民族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就具体的因缘可以用具体的方法。在学术界范围内,依于近四百余年来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几乎成为全人类普遍文化的现状,在做宗教比较研究工作时,不妨可以用比较共通的科技语言和哲学语言作为基础,例如从宇宙观和生命观、认识论和本体论等角度来进行世界各宗教义理的比较和会通研究。传统时代中国文化范围内的儒佛比较方法在今日恐怕是不适用的了。就中国文化系统内而言,欧阳竟无先生的儒佛比较是极其精彩的,以儒学为菩萨分学,佛学为全部分学;佛得儒术而佛法以普被,儒得佛法而儒道愈精深;“孔学依体之用也,佛学则依体之用而用满之体也”(《孔佛概论之概论》)。我于此领域学养甚浅,不敢论断欧阳先生之比较是否全面,但觉得是相当精辟的。
问:关於佛学研究方法论方面,当前许多学人都借助西方哲学的型态来考察,譬如:取用现象学、存在主义,乃至科学哲学的观点来探究唯识、华严之法义。这些方法,您认为可取吗?现在中国佛教的传衍,似乎只遍向於型态,有教内时贤认为,这是衰落的象征。先生对此可否详细指陈出来呢?
答:关于佛学研究方法论,当前许多研究者以西方哲学的概念和框架来考察佛学,也不失为一种研究方法,有助于具有西方哲学知识和文化背景的现代人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佛学,并且这本身就是一种比较会通的工作。我本人就是从西方哲学和科学哲学思考宇宙生命问题时接触佛学而渐趋深入的。但就佛法之“法义”本身,如我在前面所认为的,是必须有佛法本身的“体验和修持”才能比较准确地理解的,比如“般若性空”的法义,若无切身修持的当下明空的觉照体验(究竟处乃“明心见性”),仅以一般哲学去思辨,无论谓之“智慧”、“直觉”还是“本体体验”、“超越经验”,大多是似是而非、可以说是隔靴搔痒。佛学研究的根本方法就是佛法,就是“以佛法研究佛法”,就是“闻、思、修、证”。关于当前中国佛教的现状,颇多忧患,也颇多希望,但绝非衰落。其忧患处有时代社会的大因缘,其希望处,也正在时代社会的大因缘(细述恐太冗长,能否请读者参看上海《觉群》季刊2001年第1期拙文“展望21世纪佛教感言”)。佛法因缘观之活泼处,在吾人当下的一念发心,明因识缘而励力创造因缘、改变因缘,则吾人慧命幸甚、佛教慧命幸甚。未来的佛教,当是现代化的、人间化的佛教。不慧末学浅识,就先生设问之缘,不揣浅陋,谨略答如上,粗疏不当之处,恭请善知识教正。非常感谢!作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