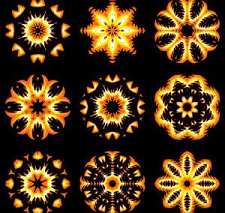唐克扬:洛阳Circa 2000——透过洛阳懂得“历史”
发布时间:2024-10-19 04:03:22作者:佛心网为什么对洛阳有种特殊的感情?这要追溯到1999年,我在芝加哥大学巫鸿老师那里念书的时候,选了一门他的课,题目就叫做“洛阳公元500年左右”(Luoyang Circa 500 A.D.)那一年,我刚去美国留学不久,谷歌和华为都立足未稳,世贸大厦仍然好好地在那站着,不知为啥手机却是努力在向小型化方向发展,和今天截然相反——世界大事像中国的房价一样即将风起云涌,我却浑然不知一头扎进了故纸堆。对我来说,“洛阳公元500年左右”也是我的“公元2000年左右”。
之前对于北朝的历史并不是全然陌生,但在北美重温洛阳的城市和艺术,则是另外一种语境了。对于大多数到美国只是为了开洋荤的中国学子而言,到美国学中国,简直是“莫名其妙”。
敦煌北朝壁画中所见城市的形象
这门课属于“研讨课”(Seminar),导师仅仅提供大题目、大方向还有方法论的指导,学生们需要自己提出问题,然后在大量阅读中寻找自己的答案。为了使得自己更充分地“浸入”,我还选了巫老师涉及北朝艺术的专题,以及另一门东亚系的课,讨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鬼”——外加旁听俞国藩教授的“中国古代宗教”。芝加哥大学的学期短,十个星期就要提交课程报告,在洋人大学的科系里,紧锣密鼓地面对如此多的中国话题,在留美十年里也算是少见了——尤其这几门课有个共性,不仅是“外国”(相对于美国而言)的,“古代”的,还是有关幽冥世界的,我们这些未知(西洋的)“生”的留学生,倒先在图书馆里“死”了一把。
在《图书馆之死》一文里,我已经吐槽过这种纯然依赖文化想象的心智生活。在图书馆中,我时常会待到午夜才回家去休息,所浏览的不外是考古发掘报告、墓志拓片、墓葬平面图之属,它们既不都是现代人心目中芳香的“美术”,也难免枯燥,常让我读得时空倒错。
北魏孝子石棺
所幸,图书馆外还是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吸引我的。就算是“学术修道院”,没有围墙的生活本身并不分“内”“外”,艺术史毕竟也还有很多具体而微的“物质文化史”的层面。最好的,是我们有一间精选的艺术阅览室“Art Reserve”,除了老师指定的读物,在那里还有很多非此不能看到的珍稀图书和精美画册,品质之精,内容之广,从那以后都没在其它地方遇到过。有时,我情不自禁地离开了本题,去翻看围绕那个时代文物主题的画片。虽然大多数书未必关于洛阳,但是它们却为我打开了一扇更广大的中古世界的大门,那些墓志、地图所记叙的世界不再那么抽象了,看累的时候,我抬起头来,就看见身边的玻璃罩里一尊北宋风格的石质佛头,金彩无存,但依然朝着我熠熠生辉地微笑。
这就是我的“洛阳Circa 2000”。
刚开始,我好生奇怪这门课为什么叫“Luoyang Circa ……”?这样一个课题的名字简直称不上名字,洛阳的公元500年,算是它的“万历十五年”吗?
后来我才知道,对洛阳而言,这是个特殊的年份,494年,孝文帝把国都自代北的平城迁到洛阳,不仅是北魏的统治者面对着巨大的变革,中国历史也迎来了一个特殊的转折时刻。在传统历史观中,孝文帝的汉化改新是“进步”的,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在客观上,却加速了这个王朝的覆亡,短短三十余年,汉魏洛阳城就匆匆地走向毁灭,并且从此一蹶不振。我们将要研究的,正是这段短促的,却又如星云般灿烂的洛阳的最后时光,在那段时间里,宗教被提升到至高无上的、足以使人迷狂的地位——在世俗的中国城市生活中,这是难见的高光的一瞬,启人想象。
我从没有去过洛阳。在此之前,就算是那些可以称得上“历史城市”的空间中,我甚至也不曾留意过“看不见的历史”——对一个还很年轻的人而言,混迹在现实的中国城市的十丈红尘中,微薄的旧痕实在是算不上有吸引力,对于庸常的生活而言,那种历史缺乏即时的,实在的意义;即使有那么一星半点的“古迹”,对于广大的“现代”的系统,也不过是汪洋大海上漂浮的一点残骸罢了。

现实中的洛阳是废墟,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很遥远的北美,“古代”却忽然变得丰满而完整了。原本只是零星的物件和遗迹,不算太多的专门研究著作,都自动连缀,组合成整体的洛阳,好像传说中它的开阳门楼柱天外飞来,不再受到彼时已在高速发展的中国现实的影响。这一切,可能还要拜修学条件太好的芝加哥大学所赐,它无需为有关遥远“古代”的课程预设什么中心思想,就像他们教授柏拉图、普林尼一样……大学只是冷不丁地把一座宝库“掼”到你的桌上,那几架子书虽然不能算是应有尽有,但几乎可以和北大图书馆阅览室里的信息量相当(当时在北大还没有办法去大库自己选书)。这些书,毕竟都是有眼力价的人细细斟酌、悉心采配的——尽管阅览室里运行着最新的苹果电脑,真正愿意在这里面壁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时候,图书馆里没有什么“现代”的动静,好让“古墓派”的人们可以独自入定,洛阳的大和小,结构和细节,逻辑与光彩,都一起涌到你的面前,自动汇成一座神话般城市的光泽与影像。
何况,关于那个洛阳,我们还有一本如此精彩而又奇特的“城市文学”著作:《洛阳伽蓝记》。
用一本书写尽一座城市原本是不容易,甚至不可能的。但是杨衒之,站在洛阳的废墟上追怀往事的北魏时人,做到了。他的空间同时也包含了时间,结构串起了故事,它们分别是“城市文学”这张华美织毯的经线和纬线。今天研究北朝洛阳的学者常常引用这本书讨论文化史,实则它的记述也有夸大之处,但是对我而言,《洛阳伽蓝记》已经足够丰富和准确了。它有关一种难得被系统记录下来的城市历史的“心理传记”,不仅有坐标方位,还有具体的故事情节。拿今天的比喻来说,就好像一整套摄像头所拍摄的各个角度的城市监控资料,在其中有着复合的,多层面的意义,难以为一般的历史叙事所尽道。
比如,大多数讨论汉魏洛阳的人都会想到永宁寺著名的九层佛塔。高达“九十丈”(一些论者认为,这个数字可以折算成现代的140米),顶上有十丈高的金色剎竿,合计离地一千尺,在距京城百里之外已能遥遥望见。《洛阳伽蓝记》用一系列的数字,不遗余力地描写这座塔的高大,比如,剎竿上有容量达二十五斛的金宝瓶,孝昌二年(526年)狂风,宝瓶被刮落在地,竟然“入地丈余”,由此可见塔得有多大,佛塔赖以传声的金铃,每一个都如小口大腹的陶瓮。佛塔九层,每一转角都悬有金铃,上下一百三十枚。佛塔四面,每面三门六窗,门上各五行金钉,全部加起来有5400 枚金钉……作者最后的总结,含有我们今天还在使用的一系列成语:
“(永宁寺塔)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议。绣柱金铺,骇人心目。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
不可思议的永宁寺塔
不惮其烦的铺陈既是歌咏曾经存在的,也是叹惋已然消逝的,这座神话般的高塔仅仅存在了16年左右,它失火的时候,当时的“消防队员”完全无能为力。当你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一定会突然醒悟这段历史文本正是基于一种“过去完成时”的黑色视角。想到中国式怀古都是这种“过去完成时”,往往都对应着“荆棘铜驼”式的不祥的预言——早在杨衒之之前,就有索靖站在洛阳宫门之前,指着宫门前的铜驼感叹说:“会见汝在荆棘中耳!”
相比如此蔚为奇观的古代的文字,永宁寺塔,就像洛阳一样,剩下的也就只有记述在考古报告中的残砖碎瓦了。我在寂寞的图书馆中大呼精彩的同时,又不免掩卷叹息……
但当我出门去,汇入大街上享受现代生活的红男绿女时,我又好像回到了另一个“洛阳”之中,只不过其间有着某种让人错乱的“时差”——图书馆里理应是回到了不甚可见的“过去”,但晨钟暮鼓的哥特式校园背后的地平线上,芝加哥市中心蔚为壮观的摩天大楼也是奇迹般地升起,好似历史摇身一变“回到未来”——更不用说,这现实和未来之间,应还有不同文明发展程度的“时差”。要知道在那一年,北京的天际线也没有发展成今天的模样。对于同样“不可思议”的资本主义世界大城市的景观,初到美国的我,还在缓慢的适应过程中。倒也不是所有的美国人对此都缺乏足够的反思,记得我们的建筑课老师讲解《癫狂的纽约》这本书时,第一个问题,就是请我们实际计算一下,假如帝国大厦内的人员需要疏散,该花多少时间?也就是99层的人要下98层楼梯,98层的人要下97层……
那座大胆的,只能造不能救的永宁寺塔,在它付之一炬时,也该有这样的算术题啊。
“不可思议”的,除了人为的奇观之外,同样涉及具体的人情。美国这样一个久未经患难,又是建立在大胆的革新和投机上的国度,大家想的都是“一万”,其实没有多少人在乎“万一”——更没有人在乎“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样的丧气话。纽约客由此和洛阳人有了某种共同的心理基础,无论多大的千古兴亡的话题,当它最终落实在“城市”这样具体的事物上面,并且同样被非常的语境所推动时,“故事”比“事实”要来得重要了,“故事”和“故事”之间,比“事实”和“事实”之间有更多的相似之处。
在黑暗中注视着大街上的灯火,我不仅下意识地感到,面前这我尚不能充分理解的异国都市的生活,和书本里的洛阳之间,也许竟然有一条神秘的时光隧道相连?
现实和过去之间,或者故事与故事之间,它们赖以连接的桥梁不是宏阔的议论,只能是更直观的东西,是可以和普通人生活对接的尺寸,触觉和感情。也就是那时候,我第一次浮现出写一部小说的念头,我要写一个古代的工匠,在标准格式的学术论文之余,补足论文里不能看见的他的心理活动。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心理活动,也就像是一面怀着创造的喜悦,一边在现实压力中苦苦补缀功课的“我”的心理活动。
洛阳“曾经”的如何如何,也就是过去所断言的“现在”的如何如何,“过去完成时”也联系着“将来完成时”。就像我们无法想象古代洛阳的壮丽,“现在”也将变成我们无法想象的废墟,我们不知“现在”将往何处去,也正如洛阳人不可能预知竟会有我们这样的子孙,在北美安静的大学里读着有关他们的故事。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就是万千个“现在”也将变成无法挽救的荆棘中的“过去”,高歌猛进的历史会有着不甚连续的时刻——“将来完成时”的预言,和“过去完成时”的追忆仿佛两面相对而立的镜子,镜子之中无穷叠映出的是城市生生灭灭的宿命。
洛阳的废墟
从那一刻起,我突然觉得我算是第一次懂得了“历史”。对我而言,洛阳不再是一个仅仅有着石窟和牡丹的旅游地了,它着实是一座古代的城市,但也以某种形式活在我们中间。有关洛阳的文学作品也不再是修辞的俗套,它记录的是具体的、可感的空间中的某一刻,即使依托它的物质载体已全然消失,你依然可以从种种痕迹中嗅到熟悉的气息,因为那也就是我们自己生活的气息。只不过这种生活并不完全是平凡的,而是充满着各种“异国情境”——恰好,我们也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异乡,同时被平庸、迷信和奇观所折磨。
于是,在2001年,当我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纽约(后来我也搬家去了那里)的世贸大厦崩塌的躯体像雨点一般砸落下来,我竟然在第一时间想起了洛阳,想起了永宁寺塔。
于是,我第一次有了去洛阳考察的机遇,那也是公元2000年后不久。其实,公元500年,那个“整数”概念对古代中国人原本是没有意义的。但是,由于以上某种冥冥中的心会,它们的实质相去并不远,既是因为围绕着那几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的事件,也是源于时间循环里产生的奇怪的“既视感”。
在现实中的洛阳,一个普通的三线工业城市,在很短的时间内,我深刻地意识到了时间所带来的丧失,“天津桥上繁华子”的风景早不复了,昔日的掖庭美人变成了粗服乱头的村姑。一切一切的落差,比想象中的还要巨大——但是对于想要“体验”历史,而不仅仅是去追怀史迹的人,这种落差又是如此地恰到好处。
从那以后,我写作论文的愿望已经不那么迫切,但写作那部小说的种种构想,就像古代洛阳一样在我的脑海中变得逐渐清晰。
作者新著《洛阳在最后的时光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