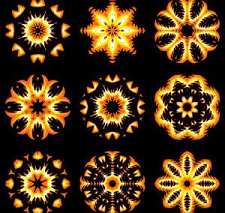佛教教育的规范
发布时间:2020-06-05 14:28:10作者:佛心网

“佛教教育”,顾名思义,就一般而言,也即从狭义上讲,应是培养僧才,续佛慧命;而从另一个角度,即广义上说,佛教本身就是教育。佛陀说法,目的是以其言教导引众生离苦得乐、转迷为悟。所以,净空法师在其《认识佛教》中说:“佛教是佛陀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
佛陀是导师,弟子是学生,经典是教材,目的是解脱自在。而二者之中,僧才教育是佛教教育的基础。原因是,每一座寺院都应当是一所学校;而每一个其中的出家人都应当是一位老师。那么,老师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整个佛教教育事业的兴衰。而素质的培养,首先是要对佛教典籍的学习,寻找一条适合自己走的路,然后循着这条路走下去,直至到达目的。从三般若的角度而言,“文以载道”。如果没有最初的文字般若作为媒介,佛教徒就无从探知甚深的实相般若之理。随之而来的,也将无从进入观照般若的真实受用,即无从同实相般若相契,也就不能感受佛法的真实。可见,佛教教育是通过文字来完成的,自然而然的应当有一个规范,即佛教教育的特殊性、随缘性,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假若无此规范,那么,佛教的教育事业就无从谈起。
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多年,回首漫漫之旅,历经兴衰曲折的因缘;面对现实的色彩缤纷,分明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尤其是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各种知识充斥和影响着人们,佛教教育怎样给自己定位?即在自己受教育,也在教育他人的过程中,找准立足之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有的佛教徒,特别是出家人,都应当给予关注和思索。有感于此,提出自己一些不成熟的想法,谨供参考。
1)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大智度论》卷二十二中说:佛法印有三种,一者,一切有为法念念生灭皆无常;二者,一切法无我;三者,寂灭涅槃。此三法印,一般以为是小乘经典的标准。《法华玄义》卷八中说,诸小乘经,若有无常、无我、涅槃三印,印之则是佛说,无三法印即是魔说。而三法印又可以通大小乘。佛教教育要依三法印建立。
2)一实相印:《法华经·方便品》中说:无量众所尊,为说实相印;嘉祥大师的《法华义疏》卷四中说:为人说于实相,印定诸法;《三藏法数》中说:盖如来所说诸大乘经,皆以实相理,印定其说,外道不能杂,天魔不能破,若有实相者,则是佛说,若无实相印,则是魔说。可见,佛教教育要依一实相印建立。只有依三法印和一实相的教育,才是佛教教育。这也正是佛教教育特殊性的土壤。否则,佛教教育的特殊性,将是无木之林,无源之水。
既是佛教教育,那么,就应当有其不共世间教育的内涵。也许会有人问,佛教教育究竟有怎样的内涵呢?回答是:应有三点,(1)、出离心;(2)、正知见;(3)、菩提心。下面就此三点分别叙述:
(1):佛教教育与世间教育有其本质的不同。世间教育在获得某一专长技能的同时,虽然也有其益于他人的一面,但却更重于功利和实惠。而佛教教育却是超越于此,乃至除人之外的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天等,因为无常、苦的缘故。既是超越,所以是出离,或者也叫出世。《金刚经三昧经》卷一中说:佛言,善男子,汝能问出世之因,欲化众生令彼众生或得出世之梁,是一大事不可思议。因此,能够使人生起出世之心,即是出离心。佛教教育应当有此内涵。如果依旧我行我素以世间价值观念为自己的价值观念,则与佛教徒身份不符。《发菩提心文》中说:观三界如牢狱,视生死如冤家,佛教徒应如是。
(2) 关于正知见:佛教教育中的正知见与世间颠倒的邪知见有别。颠倒邪知见的特点是,导致人们误入歧途。如佛陀时代的外道中,有持牛戒吃草的,有持狗戒吃粪便的,有卧荆棘修苦行的;现世的外道中,有清海的所谓“观世音菩萨法门”,有李洪志的所谓“转法轮”,有以鬼神为佛教信仰的等等。此等邪见之人自以为是,必将导致对佛教教育正知见的排斥,其结果是可悲的。佛教教育的正知见,八正道中,正见第一。《华严经》卷三十中说:正见牢固,离诸妄见。也即是指远离诸邪颠倒的正观。可见,正见即正观,或者也称中观。龙树菩萨的《中观论》中说:不生亦不灭,不一亦不异,不常亦不断,不来亦不出,能说是因缘,善灭诸戏论。此正如《大智度论》卷四十三中说的:离是二边,行于中道,是为般若波罗密。也正如《三论玄义》中说的:以无得正观为宗。或者我们也称它为空。从此可见,佛教教育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教育。至于人们以为佛教是迷信,更多的是并不了解佛教,那么,这本身就是一种迷信。至于有人因信仰佛教而误入歧途,那只能说,接受的教育的问题,因为,学佛是要“依法不依人”的。如果是依人的话,那人也一定要说佛法,不然,怎么会有“善知识难遇”一说呢?值得注意的是,佛教教育中,正知见的无得正观或空等,不是断灭义,也不是否定了事物存在的事实,只是认为这种存在不真,没有自性。
(3) 关于菩提心:菩提译为道或觉,菩提心即是指求大道或正觉之心,说得更明了一点,就是发起成佛之心称为菩提心。《维摩经·佛国品》中说:菩提心是菩萨净土。《大智度论》卷四十一中说:菩萨初发心,缘无上道,我当作佛,是名菩提心。可见,佛教徒要发起成佛之心,即“志当存高远”,才不枉是佛教徒。所以,佛教教育一定要以此为教学目的。也许在一些佛教徒看来,还不能有如此发心,或为人天,或为二乘等,但终究是开权显实、回小向大。待到有一天,因缘成熟之际,肯定要超越和升华原有的价值观念,追求最高的真谛。相比之下,如果一个佛教徒把自己的人生坐标,定在世间假相上的功利和实惠,比如升官、发财。或者是某些事业上的成功,或者是试图通过佛教的修行,来达到一些神通的技能,并以此证明这就是佛教教育,实在是一种极大的错误。尽管不能否认各有因缘,各得其所,但这已不是佛教教育的目的了。至于以佛陀教育欺世盗名,则更是与佛教的本质没有任何关系。相反,将会使佛教教育误入歧途。而佛教教育的目的,则是要我们都能成为一个圆满的觉者。能够发起成为圆满的觉心,即菩提心。若尔如此,将会使我们感到,所有的诱惑,都是旅途中的障碍,如果我们想真正接受佛教教育的话。
我们已经讨论了佛教教育的特殊性,确立了佛教教育不共世间法之处。如是,我们有了佛教教育的依止。由此看来:不能单纯地把世间教育等同于佛教教育,尽管有关系,但两者之间目的不同。也不能把相似佛教冒充于佛教。比如说,有人以佛教之名,大谈特谈抽签、算卦,见鬼、捉鬼,或者能看见什么之类,此同佛教教育的宗旨相违背,许多所谓佛教徒的信仰,基本停留在这一点上;更不能把附佛外道混同于佛教,此种外道最为危险,危害也最大。如曾经发烧一时的“佛子张晓平出山”,使多少人如痴如醉,沉湎于“万法归一功”中,导致不供佛像,只供张大师像即可。再如“清海无上师”的做怪,一个似是而非的所谓“比丘尼”,妖艳花哨,其理论是佛教、摩尼教、基督教的混合产品,拉走了多少妄想速成的人们。又如李洪志的“转法轮”,其法轮本来盗自佛教,却又说释迦牟尼临终之际说,我说法四十九年,没有说一个字,那就是还没找到真理,只有他发现的所谓“真善忍”大法才是真理。并且疯狂诋毁出家人的尊严,让他原来信佛的追随者砸毁佛像,此举绝对不应该是“真善忍”的内容。由此,规劝善良的人们,千万不要因小失大。一个人总是想得到更多的东西,但是到了最后,却连他原来拥有的那一点儿也丢失了,实在是可怜可悲!也许,许多人到了此时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发誓从此再也不学佛了。殊不知,自己根本就没有受到过真正的佛教教育,原来是在学人,而不是在学佛。如此看来,怎么能怨恨到佛教身上去呢?况且,一些人似是而非的所作所为,并不代表佛教教育的内涵。
那么,就让我们所有走过弯路的佛教徒:反思、反省、转变。反思我们的过去,反省曾经的失误,转变我们的方向,使我们信仰的基础,纳入一个佛教教育特殊性的范畴。这就需要我们深入经藏,或者听闻正法。于是,面对“邪师说法如恒河沙”的现实,我们才会正本而清源,我们才会增加免疫力,我们才会如理思维而体证佛法。
佛教教育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实在是因为佛教教育方便智的关系。前面佛教教育的特殊性,探讨的是根本智的问题,是对诸法实相的体证,此是佛教的方便智的内容,简称方便。所谓方便,指利益他人的方法,无论大小乘佛教教育,均称为方便。其中,方是方法,便是便用,即是便于运用契合一切众生的方法。《大集经》卷十一中说:能调众生悉令趣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方便;《法华经 方便品》中说:佛以方便力,示以三乘教,众生处处著,引之令得出。《三论玄义》开篇即说:适化无方,陶诱非一。可见,佛陀说法四十九年,横说、竖说,八万四千法门,针对八万四千种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其中原理无非因人而异,因机施教,应病与药。如《净名经·香积佛品》中说:
尔时维摩诘问众香菩萨,香积如来,以何说法?彼菩萨
曰,我土如来,无文字说,但以众香,令诸天人得入律行,
菩萨各各坐香树下,闻斯妙香,即获一切德藏三昧,菩萨所
有功德,皆悉具足;彼菩萨问维摩诘,今世尊释迦牟尼,以
何说法?维摩诘言,此土众生,刚强难化,故佛为说刚强之
语,以调伏之。
从以上香积佛国与娑婆世界佛陀教育众生的方法看,香积佛国因缘殊胜,众生易度,闻香即为佛事,成就菩萨所有功德;而娑婆世界因缘陋劣,众生难化,必须以因果报应、六道轮回调伏其心。就像驯服猛烈的象和马一样,一定要使用痛彻骨髓的方法,才能令其折服,虽难免有些残酷,却能使众生受益而得解脱。当然,就娑婆世界众生的根性而言,教学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就五乘而言,即人、天、声闻、缘觉、菩萨;就三乘而言,即声闻、缘觉、菩萨。此中,五乘与三乘的区别是,两者开端的因缘不同,一无出离心,一有出离心,但归根结底是相同的,只是五乘以人天为阶梯而达到出离,乃至成佛,而三乘也是摄三归一,如《法华经·化城喻品》中说:诸佛方便力,分别说三乘,唯有一佛乘,息处故说二。此中,声闻、缘觉,只是三百由旬处的化城,五百由旬的佛乘才是目的。就大小乘的教学方法而言,也有四谛与六度等等的不同,乃至戒律也有种种差异。凡此种种,均可看出佛教教育的方便,即佛教教育的灵活性。
普贤菩萨“十大愿王”中的“恒顺众生”,此恒顺即是方便,也就是随缘,即先同众生搞好关系,然后给予化导。那么,恒顺国王或者当政者,则是为了佛教的命运走向。这同样还是为了救度众生。六祖《坛经》中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犹如觅兔角。这无不告诉我们,要与现实“人际”保持良好关系,依旧是随缘的问题。东晋道安法师与前秦国王苻坚的关系,正说明了这一点。道安法师曾经说过: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因为道安法师的人格魅力,使得苻坚心仪向往。当得到道安法师之际,他们的合作,给佛教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生机。又如后赵神异的佛图澄大师,因与残暴国王石虎的良好相处,使得石虎折服并准许汉人出家,同样有利于佛教教育事业的发展。至于现实中“爱国爱教”的提倡,也一样是同现实结缘。时代的发展,历史的变迁,一切都体现着无常,如果总是以一种固定不变的眼光去看事物,佛教也不会走到今天。如果不能走到今天,也就不是佛教。所以,面对现实,佛教教育应当接受新的挑战,承当新的责任,才会有鲜活的生命力,才能够解决更多人的心理问题,也才能够被更多的人接受。现实也正在证明着这一点,近代太虚大师倡导的佛学院教育的尝试,起初遇到很多的非议和阻力。但在今天,一切都显得极其正常,并且发展良好。比如出国留学,因此获取学位,必然对佛教教育事业产生影响。相信,未来还会有新的景象出现,站在一个动的角度看,应当说是合理的。也正因为如此,佛教教育才会时时体现出活力,而不被淘汰。中国佛教的历史足迹,能够证明这一点。虽然曾经历过“三武一宗”的毁佛行为,但很快又被恢复,足见其生命力的旺盛。公元十世纪,佛教在印度本土的灭亡,其原因虽有西北雅利安人的侵入,但当时佛教的那种封闭和单纯钻研学问的风气,已同现实脱节,人们对它的存在与否,已经不感兴趣,所以说,这也应该成为佛教灭亡的一个原因。回顾往昔,不禁慨然!读史在于明理,而明理在于做人。当我们反思、反省佛教教育随缘性的时候,对于未来佛教教育事业和佛教命运走向的探索,应当有所裨益。
《中观论·四谛品》中说:若不依俗谛,不得第一义;不得第一义,则不得涅槃。此是在世俗谛上,即随缘诸法上感受佛教教育的内涵,即成就观照般若,也就是实践佛法。当然,因为因缘的有别,随缘安立了五乘与三乘等种种不同的法门,所以,在实践的过程中,虽然每一阶段归趣不同,但总的目的是开权为显实,也即是成佛。无论如何,现实生活,都是锻炼自己的好机会。因此,我们不能同现实对立起来。比如说,实践人乘佛法,必须持好五戒。而持五戒是要在生活之中去把握的,是一个人在接受一种现实的考验。只有这样,才更有意义。虽不乏被动守戒者,毕竟一些人不敢也不愿面对现实。但还是要提倡这一点。至于一乘佛法的实践,则是一个更要面对现实的历练。通过历练,在事相上,达到同不二平等的理相契。从此以后,我们将能够理解禅宗的许多机锋,同时,也能亲自感受古来大德们的心路历程。诸如,赵州禅师的“喝茶去”,百丈禅师的“野鸭子”等,此中无不体现着事相与理的统一。于是,我们终于理解了惠能大师《坛经》中所说的,“搬柴运水无非佛道,锄田种地总是禅机。”由此看来,佛教教育不应该排斥世俗诸法,它使我们在此所缘境上,加功运行,历练自心,完成自觉觉他,乃至圆满。
应当说,佛教教育的特殊性与佛教教育的随缘性都非常重要。但就次第而言,应是特殊性居先,随缘性居后。特殊性是根本,随缘性是方便。所以,佛教教育必须立足于根本,然后才能有方便。《维摩经·佛道品》中说:智度菩萨母,方便以为父,一切众导师,无不由是生。从中可以看出,智度菩萨母在前,方便以为父在后。此中,智度菩萨母比喻根本。佛教教育一定要坚持根本,即出离心,正知见,菩提心。因为,这是检验是否是佛教教育的标准。只有在这个标准的前提下,人们才能规范自己的行为,诸恶莫做,诸善奉行,佛教教育才能被世人接受,佛教才能良性发展。否则,不但谈不上什么佛教教育,就是自身的生存也有问题。当年东晋权臣桓玄,因沙门礼敬王者的问题没能如己所愿,于是,兴起整肃沙门事件。在《高僧传》卷六中记载说:俄而玄欲沙汰众僧,教僚属曰,沙门有能申述经诰,畅说义理,或禁行修整,足以宣寄大化;其有违于此者,悉皆罢遗,唯庐山道德所居,拨在搜简之列。
从中可以看出,佛教教育的特殊性不能改变。如果不是庐山僧团的良好模式,无论如何,是不能幸免的;同时,也可以感受到,当时佛教的混乱状况,尽管有桓玄的个人成见,但还是被人抓住了把柄,这里面确实有佛教徒自身的责任,应当引以为戒。如果能够掌握佛教教育的特殊性,并在现实中,严于律己,那么,这样的悲剧就不会发生。纵观历史上的毁佛事件,成为很多人的“议题”。说到此,也许有人误会,难道不能随缘了吗?回答是肯定的,不用怀疑。但佛教的随缘不是随便,不是胡作非为。出离也不是放弃,也不是不负责任。关于随缘性的问题,应是特殊性的随缘。佛教教育之所以能够随缘,完全是由佛教教育的宗旨决定的。佛教教育是要通达真谛的,而这种通达是在世俗谛上进行的,所以,佛教并不在意现实的得失,因为现实是如幻如化的不真。虽然不分别,却又要恒顺众生,不与现实冲突,即佛法不与世间相争,但也并不是向世俗投降,钻营于世间价值观念。尤其现实世界的多姿多彩,充满着不尽的诱惑,仅仅是理论上的出离,还是不能有说服力。所以,不能随便乱讲,即使说,也要在特殊性的前提下说随缘性。不然会自误误他,贻害无穷。虽然如此,随缘性的方便依然充满着活力。它可以使特殊性更好的锻炼和发挥,让特殊不再成为特殊。这是佛教教育最终要突破的一点。
只有打破了特殊与随缘界限之际,我们才会感受到:“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的惊喜。尽管到了那时,仍然要做一个令人欢喜的人。此时此景,佛教徒的内心世界一片豁达,豁达到“心包太虚”,自利利他,任运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