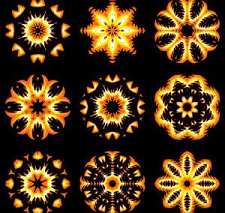论佛道儒三教伦理的交涉——以五戒与五常为中心
发布时间:2020-05-27 14:05:33作者:佛心网论佛道儒三教伦理的交涉——以五戒与五常为中心
圣凯法师
【提要】佛教深受中国固有儒家、道教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佛教。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佛教伦理与儒家伦理的交涉最为具体,并且影响到道教伦理。本文以五戒与五常为中心,着重探讨中国佛教如何理解作为在家佛教徒道德规范的五戒,尤其是各种佛教著述中五戒与五常的配对问题。我们认为,五戒与五常等的配对最早是道教提出,昙靖作《提谓波利经》时吸收了这种配对,后来成为中国佛教的通说。因此,五戒与五常的配对在一定程度上阐明了佛、道、儒三教在伦理上的交涉和相互影响。
【关键词】五戒五常提谓波利经三教伦理
一 问题的提出
按照解释人类学的说法,每一个族群都有自己的精神气质。[2]印度与中国,由于气候、地域、风土人情的不同,所以在思想信仰上有很多的差异。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必然会受到中国固有的儒家与道教文化的冲击,在不断的交涉与调和下,终于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佛教。[3]
中国传统文化对印度佛教也表示出自己的迎合与抗拒,所迎合的是以中国之人文、圆融思想而汇成佛教之圆顿宗派,所抗拒的是由于风俗习惯的不同而导致的伦理、道德观点方面的差异。面对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抗拒,佛教不得不作出自身的调整与妥协,同时也促进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中国佛教伦理与儒家伦理的交涉最为具体、明显。同时,二者交涉还影响到了道教伦理的发展。
虽然海内外学界已经对中国佛教伦理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4],但是在一些问题上仍有待于深入,因此我们以五戒与五常为中心来探讨中国佛教伦理与儒家伦理的交涉与融合问题。因为五戒作为在家佛教徒的道德规范,在普及五戒的过程中,为了能够使中国民众接受佛教的戒律,中国佛教便与儒家的「五常」配对,出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阐释。同时,为了增加说法上的神圣性,还出现了《提谓波利经》。
五戒,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是在家优婆塞、优婆夷所受持的五条制戒。因为五戒是一切佛戒的基础,进入佛门之后的在家弟子便应受持,所以通常称为「在家戒」。劳政武先生认为,五戒的前四戒具有「自然法」性质[5],因为五戒是「五大施」[6],所谓:「五戒法是三世诸佛之父,依五戒而出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7]
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规范。这是董仲舒在对汉武帝的第一次策问时提出的:「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五者修饰,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8]五常之道是董仲舒的创造,孔子思想体系中虽有「仁」、「义」、「礼」、「智」、「信」诸范畴,但并未将其连用,更未从价值体系建构的理论高度、从道德论层面明确予以论述。孟子虽然把仁、义、礼、智看作人们不可或缺的四种品德,但并未将信与四德并提。[9]董仲舒主要借助于《公羊春秋》的「五[10]其比,偶其类」[11]的主观模拟方法,一方面通过把自然现象拟人化,赋予自然现象以道德的属性,把自然规律和伦理法则相混同,从而把自然界的一切看作是「天」有意识、有目的的安排,特别是自然变异,更被视为「天意」的突出表现;另一方面,又通过把社会关系神秘化,赋予社会现象以神学的含义,宗法封建制的各种等级名分和隶属关系都被说成是在「名号」中表达了「天意」。[12]所以,他用五行来比附「五常」及人身的五脏,这对后来中国佛教在解释五戒时影响十分巨大。
其实,五戒作为佛教的道德规范,五常作为儒家的道德规范,二者在基础、目标、形式、重点方面有相当大的不同。[13]如:不杀生可以说是仁的一种具体表现,但不能说「不杀生」等于「仁」,因为「仁」的外延大太多了。又如,不饮酒虽然含有「礼」与「智」的精神,但是儒家的「礼」与「智」绝不等于佛教的不饮酒戒,因为儒家并不戒酒。虽然二者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毕竟有一种相近相接的趋势。所以,中国佛教在弘扬五戒的过程中自然与五常相配对。那么,二者是如何配对的?二者的配对在儒、佛的关系上表现出怎样的倾向?[14]另外,在道教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这种配对,这又表现出了佛、道、儒三者是怎样的关系?在三教中,这种配对最早是由哪一种最早发明的?
我们正是基于上述的问题,在先贤前辈的指引下,对五戒与五常的配对进行深入研究,希望通过我们的研究能够加深了解儒、佛、道三教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能从另一侧面说明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二 有关五戒的经典及其疑伪经典
有关五戒,最早在《阿含经》中出现,如《中阿含》卷二十八中的《瞿昙弥经》、《长阿含经》卷二的《游行经》、卷十一的《善生经》、《增一阿含》卷二十三的《增上品》。[15]另外,在《出三藏记集》卷二,我们看到有宋求那跋摩翻译的《优婆塞五戒略论》一卷、《三归及优婆塞二十二戒》一卷,后凉昙无谶翻译的《优婆塞戒经》七卷;在《出三藏记集》卷四「失译」中,有《贤者五戒经》一卷、《优婆塞五戒经》一卷、《三品弟子经》一卷、《戒消灾经》一卷、《灌顶三归五戒带佩护身咒经》一卷、《三归五戒神王名》一卷、《五戒报应经》一卷、《道本五戒经》一卷。[16]
从东晋到南北朝初期,有关五戒的经典相继译出,同时,有关出家戒及菩萨戒的经典也逐渐译出,如罗什所译《梵网经》、竺佛念所译《菩萨璎珞本业经》、求那跋摩所译《佛说菩萨内戒经》、《菩萨善戒经》、昙无谶所译《菩萨地持经》及失译《在家菩萨戒经》、《在家律仪经》等。因为五戒通大、小乘戒律,这些菩萨戒经的传播推动了五戒的流行。
随着五戒的流行、实践者的增多,在五戒的阐释及理论方面必定有进一步的要求。于是,出现了有关五戒的疑伪经。[17]因为了解五戒持犯的要求的进一步提出,所以首先从律部中采摘撰述成经典。如依《十诵律》撰成《佛说优婆塞五戒相经》,从《优婆塞五戒威仪经》中撰成《离欲优婆塞优婆夷具行二十二戒》。[18]这完全为了佛教徒本身持戒及了解戒相的需要,是佛教内部的自我要求。
五戒毕竟是佛教的伦理道德,佛教徒生活在社会中,肯定会受到来自儒家的纲常伦理的强大压力,所以.,如何将五戒与儒家的五常调和是佛教弘扬者必须解决的问题。道端良秀先生认为,五戒与五常在数目上都是五,数目的一致是突破口。[19]因为从汉代以来,「五[20]其比,偶其类」的主观模拟方法非常盛行,五戒与五常一致便能进一步与五星、五岳、五脏、五经、五德、五色、五行、五阴等配合,这样就符合了中国的思想,成为中国人理解佛教的最好手段。所以,这种数目的一致为五戒与五常等的配合提供了最好的前提,也为《提谓波利经》的创作提供了条件。
三 《提谓波利经》中的五戒、五常
对于《提谓波利经》的研究,随着敦煌遗书的发现,国际学界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21]我们在前辈的基础上对该经中的五戒与五常关系进行考察,旨在阐明该经所体现的佛教伦理与儒家伦理的交涉与融合。
北魏时代,在太武帝灭佛以后,佛教得到了急速的发展。外域传来的各种经典大部分已经遭受焚毁,几乎没有经典可以作为依据,即使残存的一些,也不足指导北魏庶民,所以出现了大量的疑经。《提谓波利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最早见于《出三藏记集》卷五,说是「北国比丘昙靖撰」。[22]后来,《历代三宝纪》卷九也将之断为疑经:
《提谓波利经》二卷,见《三藏记》。右一部,合二卷,宋孝武世,元魏沙门释昙静[23]于北台[24]撰。见其文云:东方太山,汉言代岳;阴阳交代,故云代岳。于魏世出,只应云魏言,乃曰汉言,不辨时代,一妄;太山即此方言,乃以代岳译之,两语相翻,不识梵魏,二妄。其例甚多,不可具述,备在两卷经文。旧录别载,有《提谓经》一卷,与诸经语同,便靖加足五方、五行,用石糅金,致成疑耳。[25]
昙靖二卷本《提谓经》是在一卷本的基础上编成的,同时吸收了五方、五行等中国思想,出现了以「汉」代「魏」、称「代岳」为「太山」的错误。
道宣《续高僧传》吸收了《历代三宝纪》的说法,并提到隋开皇年间[26]关中地区的民众曾成立学习《提谓经》的义邑,在家信众,每月持衣钵,经营斋会,以正律为规范,相互检束,守戒行,云集多人,可见这部经的影响力。[27]
《提谓波利经》已经散佚,但是其内容在后来的佛教著作中多有引用,冢本善隆曾经整理这些佚文。[28]后来,在敦煌遗经中发现了该经的残本。[29]牧田谛亮先生曾对后汉安世高所译《佛说分别善恶所起经》与《提谓经》进行比较,认为有部分相似。[30]而《佛说分别善恶所起经》在《出三藏记集》卷四被列入「失译」类,《历代三宝纪》卷四才录为安世高所译[31],但是《法经录》、《彦琮录》、《静泰录》都不认为是安世高所译,是中国自撰疑经之一。所以,到底哪部经典时间在前很难判断。[32]但是,根据《出三藏记集》等说法,《提谓经》应该有一卷本真经,然后昙靖依一卷本增加阴阳、五行之说,采取世俗一般的信仰,而杂以道术家的说法,从而撰成二卷本《提谓经》。[33]
提谓与波利是佛教史上最早归依佛陀的两位商人,在《太子瑞应本起经》、《普曜经》、《修行本起经》中都有记载。当时,佛陀在菩提树下成佛后,提谓与波利率领五百商人经过,捧食供养,并归依佛。《提谓波利经》就是以此为线索编纂而成,结合汉儒的阴阳五行、伦理纲常和道教的延命益寿说明五戒、十善、六斋日、三长斋月、八王日等在家修行方法。
《提谓经》十分重视五戒,对五戒给予极高的地位。如P.3732中说:
五戒甚深弥大,其神神妙,无物不生,无所不成,无所不入,九弥八极,细入无间,变化无时,像无像之像,五戒之神,起四色之未形,故为天地之始、万物之先、众生之父、大道之根,五戒是也。
实际上,《提谓经》对五戒的阐述已经把五戒看成是至高的精神本体,具有老庄思想中「道」的性质。
前面我们曾经提到,五戒之所以能融合中国固有的思想,是因为数目上的一致性。智顗《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疏》卷二引用《提谓经》说:
提谓、波利等问佛:何不为我说四、六戒?佛答:五者,天下之大数。在天为五星,在地为五岳,在人为五脏,在阴阳为五行,在王为五帝,在世为五德,在色为五色,在法为五戒。以不杀配东方,东方是木,木主于仁,仁以养生为义;不盗配北方,北方是水,水主于智,智者不盗为义;不邪淫配西方,西方是金,金主于义,有义者不邪淫;不饮酒配南方,南方是火,火主于礼,礼防于失也;以不妄语配中央,中央是土,土主于信,妄语之人乖角两头、不契中正,中正以不偏乖为义。[34]
该经指出,佛说五戒是因为五是天下大数,由于数目上的一致,所以能够与五常、五方、五行等配合,所以《提谓经》能够深受中国人接纳。在P.3732中详细地提到了五戒配五帝、五行、五方、五星、五脏:
长者提谓白佛言:神在五脏,用事之何?佛言:五藏[35]之神,所住各异,肝行仁,心行礼,肺行义,肾行智,脾行信。此五行者,天地之大用。天失之妖灾起,地失之万物不生,四时失之阴阳不和,王者失之天下乱,人民失之灭姓[36]命、身危亡,神气失之五脏不治、发狂死亡。
根据《提谓经》的叙述,我们可以列表如下[37]:
五戒
五常
五行
五方
五星
五脏
不杀生
仁
木
东方
岁星[38]
肝
不偷盗
智
水
北方
辰星[39]
肾
不邪淫
义
金
西方
金星
肺
不妄语
信
土
中央
镇星[40]
脾
不饮酒
礼
火
南方
荧惑[41]
心
其实,数目的使用是非常早的,它是古人对现象反复归类的结果,他们把「相似与相近的归为类、序为数,这类与数,一经一纬,便成了初民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42]在商周时代甚至更早的时间,古人按照自己的体验、想象与观察,把相当多的复杂现象都归结成「五」和「类」,并且常常把宇宙间各种各样的「五」和「类」互相搭配起来,用五个最基本的象征来指代它们,并且想象它们都有一定的对应性和相似性。这样,「五」这个数字就似乎有不言而喻的意义。当然,五行思想的来源可能要到战国后期。[43]在鲁昭公时代,这种思想已经很系统、很普遍了。[44]
正是在这种数的强大中国传统下,在来自儒家、道家对佛教违背纲常伦理的强烈攻击下,同时刚好五戒与中国的「五」数目一致,所以将五戒与五常等相比附是很自然的事。但是,从有关中国佛教著述所引用的《提谓经》佚文来看,五戒与五常配对的顺序不大一样。如湛然《止观辅行传弘决》卷六之二[45],我们将其所说内容列成表格如下:
五戒
五常
五行
五方
五脏
五官
不杀生
仁
木
东方
肝
眼
不偷盗
义
金
西方
肺
鼻
不邪淫
礼
水
北方
肾
耳
不妄语
信
土
中央
脾
身
不饮酒
智
火
南方
心
舌
《金光明经文句》的说法与《止观辅行传弘决》相同:
提谓经云:五戒者,天地之大忌,上对五星,下配五岳,中成五脏,犯之者,违天触地、自伐其身也。又对五常:不杀对仁,不盗对义,不淫对礼,不饮酒对智,不妄语对信。又对五经:不杀对《尚书》,不盗对《春秋》,不淫对《礼》,不妄语对《诗》,不饮酒对《易》。又对十善:杀盗淫是身三,妄语摄口四,饮酒摄意三。[46]
《金光明经文句》不仅将五戒与五常配对,而且与五经、十善配对。
另外,吉藏《仁王般若经疏》所引《提谓经》的佚文则与智顗的《仁王护国般若经疏》完全一样。[47]法琳《辩正论》所引佚文五戒与五常的配对与智顗《仁王经疏》相同,但是说法又有所不同:
提谓经云:不杀曰仁,仁主肝,木之位;春阳之时,万物尽生,正月、二月,少阳用事;养育群品,好生恶杀,杀者无仁。不邪曰义,义主肺,金之位;七月八月,少阴用事;外防嫉妒危身之害,内存性命竭精之患,禁私不淫,淫者无义。不饮酒曰礼,礼主心,火之位;四月、五月,太阳用事;天下太热,万物发狂,饮酒致醉,心亦发狂。口为妄语,乱道之本,身致危亡,不尽天命,故禁以酒,酒者无礼。不盗曰智,智主肾,水之位;十月、十一月,太阴用事;万物收藏,盗者不顺天,以得物藏之,故禁以盗,盗者无智。不妄曰信,信主脾,土之位;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中央用事;制御四域,恶口伤人,祸在口中,言出则殃至,气发则形伤,危身速命,故禁以舌,舌者无信。[48]
「仁」因为好生恶杀,相当于「不杀」;「义」因为防害不淫,相当于「不邪淫」;「酒」因为乱辞无礼,常不饮酒即是「礼」;盗是因为无智而不顺天;「智」相当于「不盗」;「信」相当于「不妄语」。《辩正论》除了五戒与五常相配对以外,还结合了四季、十二个月等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体系。
综合以上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后来佛教界在吸收《提谓经》时是各取所需,由于立足点的不同,各自形成自己的体系。这样,总共形成了三种体系:第一,是吉藏、智顗《仁王经疏》;第二,《金光明经文句》及《止观辅行传弘决》;第三,《辩正论》。第一种体系是从五戒方面来调和五常,所以顺序为「仁、智、义、信、礼」;第二种是以五常为立足点反过来调和五戒,顺序为「仁、义、礼、智、信」;第三种,《辩正论》是在第二种基础上变五戒而配五常。不管配对的顺序如何,五戒与五常已经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了,所以《提谓经》把违犯五戒视为「不忠不孝」而加以谴责。如P.3732
佛言:人不持五戒者为无五行。煞[49]者为无仁,饮酒为无礼,淫者为无义,盗者为无知[50],两舌者为无信,罪属三千。先能行忠孝,乃能持五戒;不能行忠孝者,终不能持五戒。不忠、不义、不孝、不至[51],非佛弟子。
由于忠、孝等伦理道德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所以《提谓经》不仅将五戒与五常相配对,而且将忠、孝等摄入五戒中作为五戒的初门,这样便解决了二者在伦理上的冲突。同时,将忠、孝这些伦理道德与佛教的因果报应理论联系起来加强了说服力。如P.3732:「不孝父母,为臣不忠,为父不仁,为母不慈,为君不平,为臣不顺,为弟不恭,为兄不敬,为妇不礼,为夫不贤,奴婢不良,死入地狱。」S.2051中说,犯五戒者死后「入太山地狱中」。
《提谓经》虽然被后来的经录家认定为疑经,但是它表现了中国人对佛教的理解及其佛教自身对中国思想的适应,所以仍然被后来的佛教著述者经常引用,而五戒与五常的配对则成了中国佛教的显著特征。
四 五戒与五常的配对在中国佛教的流行情况
对于五戒与五常配对,自从经过《提谓经》的创造以后,对中国佛教影响极大。除了我们以上所引著作以外,提倡者代不乏人。
南齐沈约[52]在与道士陶弘景论争时著《均圣论》,指出佛教的五戒也是儒家典籍所禁止,说佛教不杀生戒的精神早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即已具足,但是佛教为了实践慈悲,特别重视不杀生戒至为明显。周公与孔子说仁义,相对地,佛教则说不杀生的慈悲。佛教的慈悲与周孔之教是不矛盾的。[53]但是,很明显,沈约并没有看到《提谓经》,只是意识到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仁义是不矛盾的。
最早接受五戒与五常的配对应该是北齐的颜之推[54]。他在《颜氏家训‧归心篇》中说:
内外两教,本为一体,渐极为异,深浅不同。内典初门设五种之禁,与外书五常符同。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55]
颜之推将五戒与五常配对无非是为了调和儒家与佛教,这是接受了《提谓经》的影响,并非参考了沈约的说法。[56]因为,昙靖撰《提谓经》是受昙曜的指导,而昙曜是北魏佛教的复兴者,所以应该很快得到流传,颜之推应该会受到影响。
同时,北齐魏收《魏书‧释老志》在解释佛教时开头便说:「又有五戒去杀、盗、淫、妄言、饮酒,大意与义、礼、智、信同名为异耳。云奉持之,则生天人胜处;亏犯,则坠鬼畜诸苦。」[57]这已经论述到五戒与五常的一致,二者是「同名为异」,可见与《提谓经》的关联。
将五戒与五常、五行结合起来,经常引用《提谓经》,主张五戒、五常一致的,最早是天台智顗,因为沈约、颜之推并没有直接引用《提谓经》。他在《摩诃止观》卷六说:
若深识世法,即是佛法。何以故?束于十善即是五戒,深知五常、五行义亦似五戒。仁慈矜养,不害于他,即不杀戒;义让推廉,抽己惠彼,是不盗戒;礼制规矩,结发成亲,即不邪淫戒;智鉴明利,所为秉直,中当道理,即不饮酒戒;信契实录,诚节不欺,是不妄语戒。周、孔立此五常为世间法药,救治人病。又五行似五戒:不杀防木,不盗防金,不淫防水,不妄语防土,不饮酒防火。又五经似五戒:《礼》明撙节,此防饮酒;《乐》和心,防淫;《诗》风刺,防杀;《尚书》明义让,防盗;《易》测阴阳,防妄语。如是等世智之法,精通其极,无能逾,无能胜,咸令信伏而师导之。[58]
智顗是以五常、五行、五经为立足点来会通五戒,他虽然没有引用《提谓经》的说法,但是他的配对与《提谓经》并没有什么不同。
到了唐代,特别是唐朝初期,由于傅奕发起对佛教的攻击,于是,儒、佛、道三教的争论变得十分激烈。[59]所以,佛教与儒家伦理的交涉、融和便显得十分必要和盛行。除了法琳《辩正论》直接引用《提谓经》以外,我们在道世《法苑珠林》卷八十八《五戒部》的「述意部」中也发现了他对五戒与五常的配对:
夫世俗所尚仁、义、礼、智、信也,含识所资不杀、盗、淫、妄、酒也。虽道俗相乖,渐教通也。故发于仁者,则不杀;奉于义者,则不盗;敬于礼者,则不淫;悦于信者,则不妄;师于智者,则不酒。[60]
道世认为,五戒与五常的关系是一种因果法则,五戒为因,五常为果,受持五戒,五常便自然显现。所以他说:「受持不杀之因,自证乎仁义之果。」
唐代中期,除了天台宗的湛然引用《提谓经》说明五戒与五常的配对以外,华严宗的宗密《原人论》也说:「佛且类世五常之教,令持五戒。」他认为,不杀是仁,不盗是义,不邪淫是礼,不妄语是信,不饮酒是智。[61]众所周知,宗密是有名的禅教一致论的倡导者,同时他还调和儒、佛、道三教,引用《父母恩重经》认为,佛教十分强调孝道,以对抗儒、道二家对佛教的指责。后来,《原人论》的批注者净源、圆觉继承宗密的思想,对五戒与五常的配对进行了进一步的阐明。[62]
宋代契嵩在宋仁宗明道年间[63]针对欧阳修等人辟佛的议论作《辅教编》,阐明儒、佛一贯的思想,轰动了当时文坛。契嵩盛赞儒家五经,以佛教的「五戒」等同于儒家的「五常」,提出「孝为戒先」的重要命题。他认为,五戒与儒家的五常仁义是「异号而一体」[64]。他说:
夫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言,信也。是五者修,则成其人、显其亲,不亦孝乎!是五者有一不修,则弃其身、辱其亲,不亦不孝乎!夫五戒,有孝之蕴而世俗不睹,忽之而未始谅也。[65]
契嵩认为,五戒与五常是一体的,只是在名称上有所差别而已。同时,他还把五戒上升到「孝」的高度,认为持五戒便是孝,不持五戒便是不孝。这样,五戒便与儒家的根本伦理「孝」具有同一的水平。
自从《提谓经》提出五戒与五常的配对以后,这种配对已经成为中国佛教的通说,成为佛教调和儒家、道教的有力工具。
五 道教的五戒与五常
作为中国本土的传统宗教,道教与佛教的关系历来十分复杂,二者相互吸收、相互影响对各自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道教的戒律,至少就其形式而言,显著地有来自佛教的影响。[66]
作为道教的五戒有四种形式:升玄五戒、洞神五戒、正一五戒两种。[67]在这四种五戒中,正一五戒的其中一种提到五戒与五常的配对:1)行仁,慈爱不杀,放生度化,内观妙门,目久久视,肝魂相安;2)行义,赏善伐恶,谦让公私,不犯窃盗,耳了玄音,肺魄相给;3)行礼,敬老恭少,阴阳静密,贞正无淫,口盈法露,心神相和;4)行智,化愚学圣,节酒无昏,肾精相合;5)行信,守忠抱一,幽显效微,不怀疑惑,始终无忘,脾志相成。[68]可见,道教的五戒与五常相结合,五常为因,五戒为果。就是说,由于奉持五常,所以能够受持五戒。
在道教的另一部经典《太上老君戒经》中说:
老君曰:五戒者,天地并始,万物并有;持之者吉,失之者凶;过去成道,莫不由之,故其神二十五也,经文五千是其义也。老君曰:五戒者,在天为五纬,天道失戒,则见灾祥;在地为五岳,地道失戒,则百谷不成;在数为五行,五数失戒,则水火相薄、金木相伤;在治为五帝,五帝失戒,则祚天身亡;在人为五脏,五脏失戒,则性发狂。老君曰:是五者,戒于此而顺于彼。故杀戒者,东方也,受生之气尚于长养,而人犯杀,则肝受其害;盗戒者,北方也,太阴之精主于闭脏,而人为盗,则肾受其殃;淫戒者,西方也,少阴之质,男女贞固,而人好淫,则肺受其沴;酒戒者,南方火也,太阳之气,物以之成,而人好酒,则心受其毒;妄语戒者,中央土德信,而人妄语,则脾受其辱。[69]
在这部道教的经典中,五戒与五行、五脏、五方等结合在一起,这与《提谓经》基本上是相同的。
对于这种五戒与五常的配对,《太上老君戒经》与《提谓经》哪个更早?学术界没有定论。[70]我们不揣浅陋,不妨对此作些探讨。
我们知道,北魏太武帝灭佛以后,佛教经典[71]极其缺乏,为了适应民众信仰佛教的要求,昙靖编撰了《提谓经》。当时,佛教戒律的传授有诸多欠缺,甚至需要向道士学习。《高僧传》卷十一《志道传》说:
先时,魏虏灭佛法,后世嗣兴而戒授多缺。道既誓志弘通,不惮艰苦,乃携同契十有余人往至虎牢,集洛、秦、雍、淮、豫五州道士会于引水寺,讲律明戒,更申戒法。伪国僧禁获全,道之力也。[72]
这充分显示了当时的道教道士对佛教的戒律具有一定的研究水平。所以,志道才要会集五州道士,向他们学习佛教的戒律。而道教戒律的兴盛,北魏灭佛的主谋之一寇谦之有莫大的功劳。寇谦之是北魏道教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他在神瑞二年[73]撰写了《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后来,他得到北魏太武帝的支持,完成了其改革的任务。他改革的总原则是:以礼度为首。凡是合乎儒家礼教的就,保留、增益;违背儒家礼教的,就革除、废弃。[74]所以,他增订了道教的戒律,吸收了佛教的形式,而其内容则主要是儒家的伦常道德,如忠、孝、仁、义等。因为他所著的《老君音诵诫经》只残存很少一部分,我们很难窥其全貌,所以并没有看到他对五戒与五常等的配对。
不过,阴阳五行的思想在道教中相沿已久,在早期上清派所崇奉的最主要经典《大洞真经》中已有这方面的影响。该经的卷一叙述了存思五方之气的思想是以东、南、西、北、中五方为基础,配以五行、五气、五色、五脏。[75]我们将其配对列表如下:
《大洞真经》的说法与古灵宝的《五篇真文》和《五阴符》十分相似[76],可见道教对阴阳、五行等的配对十分重视。所以,我们想到了寇谦之时代为了增订道教的戒律而对各种思想进行系统化,便会出现以「五」为中心的配对,这正好适合了其儒、佛、道一体化的新天师道思想。
我们认为,五戒与五常、五行等的配对最早来自道教,而寇谦之更是这种配对的有力推动者。从道教方面来说,既要吸收佛教戒律的形式,又要以儒家的伦理纲常为内容,有必要对二者进行一些会通工作。同时,北魏灭佛以后,佛教界为了复兴佛教,也必须向道教学习,佛教在戒律方面的欠缺更是突出的问题。所以,昙靖在作《提谓经》过程中为了融合儒家伦理等到中国传统思想而自然地吸收了道教有关五戒的配对思想。
至于道教的《太上老君戒经》的编撰时代,目前没有定论。但是,这部经典是老君向尹喜传授的,这是「老子化胡说」与佛教五戒结合的产物。《太上老君戒经》其实包括经典原文与批注,在「老君西游,将之天竺」,注云:「周幽王之末也,周而西之于天竺。天竺,国名也。事出《玄妙内篇》」。[77]《玄妙内篇》是最早记载「老子化胡说」的道经,其时间大约在430年前后。[78]而批注只引用了《玄妙内篇》而不引用《三天内解经》、《西升经》、《老子化胡经》,可见《太上老君戒经》应该在《玄妙内篇》之前,即在430年以前。同时,批注中两次出现了「上清法」,表明这部经是属于上清派的作品。
《无上秘要》编纂于北周末年,是北周武帝企图齐一圣人之道、建立经教体系的产物。[79]所以,对于道教的五戒与五常配对,《无上秘要》自然要加以引用。
通过以上的考察,我们认为,五戒与五常、五行等配对最早来自道教,而且,很可能来自上清派之手。后来,北魏太武帝法难以后,昙靖在制作《提谓经》过程中吸收了道教的说法。
六 五戒与五常配对中的佛、道、儒关系
由于五戒与五常、五行等在数目上的一致性,所以五戒作为佛教的伦理道德才有可能融进中国文化固有的思想中。最早将五戒与五常、五行等进行配对的,我们认为,应该是道教,其时间下限应该为公元430年。
道教作为中国本土的传统宗教,在伦理道德上直接采用了儒家伦理,并且认为,自身与儒家一起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从而攻击作为外来文明的佛教。道教是在形式上吸收了佛教的戒律,而其内容则是儒家的伦理,因此才会对五戒与五常、五行等进行配对。但是,这种配对恰好符合了佛教与中国文化调和的需要,所以北魏昙靖在制作《波利提谓经》过程中便吸收了五戒与五常等的配对思想。因为佛教作为外来宗教,由于地域、风俗等的差别,在伦理道德上与中国文化存在着许多差异,所以,佛教传入中国后自然便受到这方面的压力与指责,在伦理道德上,佛教很自然地向儒家靠拢,创造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伦理,如孝道说、五戒与五常的配对等。从这种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出佛教是自觉地转变自身的形态,以此来调和、适应儒家。
五戒与五常的配对形成了三种体系:第一种,吉藏、智顗《仁王经疏》体系是从五戒方面来调和五常,所以顺序为「仁、智、义、信、礼」;第二种,《金光明经文句》、《止观辅行传弘决》是以五常为立足点反过来调和五戒,顺序为「仁、义、礼、智、信」;第三种,《辩正论》是在第二种基础上变五戒而配五常。后来,第二种体系成了中国佛教的通说,对后来中国佛教伦理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其实,五戒与五常的配对,其前提是数目上的一致性,是佛、道、儒三教在伦理上交涉与融合的产物。在五戒与五常配对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儒、佛、道三教的关系及其各自的发展。
[1] 作者圣凯,1972年生。
[2] 解释人类学的代表克里福德‧基尔兹指出:一个族群的精神气质是指他们生活的一种风气、特征、品性,是其道德与审美的方式与基调,标示着此一族群对他们自己和他们所处世界的根本态度。精神气质与世界观念不仅互相影响,而且可以说,二者互为基础。Clifford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Basic Books,1973,pp126~127.
[3] 李志夫先生提出「漩涡理论」,将佛教中国化比喻为一条江河:中国有似一座新的河床,印度佛教有似河水;当其注入新的河床后,就会受到新的河床所规约,受到中国文化、思想、制度乃至改朝换代之冲击,而形成各种大小之漩涡,而成为中国的佛学与佛教。相对地,中国佛教为一「次大漩涡」,其文学艺术为小漩涡。见《佛教中国化之进程》,杨曾文、方广锠编《佛教与历史文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27页。
[4] 王月清《中国佛教伦理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
[5] 所谓「自然法」,是指人类社会基于人类普遍理性而产生的一些最高最基本的「法律原则」。见劳政武《佛教戒律学》,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99页。
[6] 因为持五戒而能持到彻底绝不仅止于止恶,当能做到行善。不杀生而要护生与救生,不偷盗而要行布施。其余三戒,亦可准知。见释圣严《戒律学纲要》,台北东初出版社1988年第8版第55页。
[7] 清‧弘赞《归戒要集》卷中,《卍续藏》第107册第137页。
[8] 《汉书》卷56《董仲舒传》,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1版第1册第599页。
[9] 李宗桂《论董仲舒的价值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中国哲学的诠释与发展——张岱年先生九十寿庆纪念论文集》第152~153页。
[10] 通「伍」。
[11] 《玉杯》
[12] 肖萐父、李锦全主编《中国哲学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303~304页。
[13] 劳政武《佛教戒律学》第365~367页。
[14] 这种配对显示出中华文明对待外来文明的态度。
[15] 见大野法道《大乘戒经□研究》第379页,理想社,东京,1954年。
[16] 在《大正藏》卷二四中,求那跋摩所译《优婆塞五戒相经》就是《优婆塞五戒论》,《优婆塞五戒威仪经》就是「失译部」的《优婆塞五戒经》。《大正藏》卷十七《佛说弟子三品经》、卷二四《佛说戒消灾经》,《历代三宝纪》卷五、《开元释教录》卷二将「失译」变成支谦所译。
[17] 「疑伪经」是相对于从印度、西域传来的翻译经典说的,指中国人所创作的经典。有关疑经的研究见牧田谛亮《经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6年版。牧田谛亮先生将疑经撰述的意图分为六类:1)迎合主权者的心意;2)批判主权者的施政;3)为了与中国传统思想调和或将之跟佛教比较优劣;4)喜欢特定的教义信仰;5)标示现存特定某个人的名;6)疗病、迎福等迷信类。
[18] 见大野法道《大乘戒经□研究》第383~386页。
[19] 道端良秀《唐代佛教史□研究》第361页,法藏馆,京都,1957年。
[20] 通「伍」。
[21] 如冢本善隆《支那□在家佛教特□庶民佛教□一经典——提谓波利经□历史》,收在《支那佛教史研究‧北魏篇》,弘文堂书房,东京,1942年;后又收入《北朝佛教史研究》,《冢本善隆著作集》第2卷,大东出版社,东京,1974年版。还有,如道端良秀《唐代佛教史□研究》、牧田谛亮《疑经研究》、望月信亨《佛教经典成立史论》(法藏馆,京都,1978年版)、鎌田茂雄《中国佛教通史》第4卷(佛光出版社译,佛光出版社,台湾,1993年版)、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版)。
[22] 《出三藏记集》卷5,《大正藏》卷55,39a。
[23] 通「靖」。
[24] 按:平城,今山西大同。
[25] 《历代三宝纪》卷9,《大正藏》卷49,85b。
[26] 581~600年
[27] 《续高僧传》卷1,《大正藏》卷50,428a。
[28] 冢本善隆《北朝佛教史研究》第202~208页,澄观《华严玄谈》卷四,道世《法苑珠林》卷二十三、三十七、八十八,日本证真《法华玄义私记》卷十,智顗《法界次第初门》上之下、《法华玄义》卷十、《仁王护国般若经疏》卷二,湛然《止观辅行传弘决》六之二,法琳《辩正论》卷一,窥基《大乘法苑义林章》卷一、《类聚三代格》卷二《年分度者事‧宽平七年太政官符》,后周义楚《义楚六贴》卷六,新罗太贤《梵网经古迹记》卷四,等。
[29] 敦煌本《提谓波利经》有四种:S.2051(《佛说提谓经》卷下),P.3732(相当于卷上),B.7146(霜015)《佛说提谓五戒经并威仪》,苏联亚洲民族研究所所藏敦煌本。
[30] 牧田谛亮《疑经研究》第149~150页
[31] 《历代三宝纪》卷4,《大正藏》卷49,51a。
[32] 鎌田茂雄先生认为时间的先后难以判断(《中国佛教通史》第4卷第202页),而任继愈《中国佛教史》则从文字看当早于《提谓经》,说明《提谓经》在编造中也抄录了当时所存的经典,见该书第556页。
[33]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第1版第584~585页。
[34] 《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疏》卷2,《大正藏》卷33,260c~261a。
[35] 通「五脏」。
[36] 通「性」。
[37]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557~558页
[38] 木星
[39] 水星
[40] 土星
[41] 火星
[42] 庞朴《主法与杂多》,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学人》第6辑。
[43] 有关五行的这种情况,易学专家汪显超博士在《〈三坟易〉略论》一文中有详细的述及,见《世界弘明哲学季刊》2000年12月号,国际网址:www.whpq.org、www.whpq.net
[44] 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国思想史》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41、157页。
[45] 《止观辅行传弘决》卷6之2,《大正藏》卷46,341c~342a。
[46] 《金光明经文句》卷1,《大正藏》卷39,50b~c。
[47] 《仁王般若经疏》卷上1,《大正藏》卷33,319a~b。
[48] 《辩正论》卷1,《大正藏》卷52,494c。
[49] 通「杀」。
[50] 通「智」。
[51] 通「智」。
[52] 441~513年
[53] 《广弘明集》卷5,《大正藏》卷52,121c。
[54] 531~590年
[55] 《广弘明集》卷3,《大正藏》卷52,107b。
[56] 道端良秀先生认为,颜之推是参考了沈约的说法而展开的。(《唐代佛教史□研究》第366页)
[57] 《魏书》卷114《释老志》,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1版第3册第2504页。
[58] 《摩诃止观》卷6上,《大正藏》卷46,77b。
[59] 见李斌诚《唐前期道儒释三教在朝廷的斗争》,杨曾文、方广锠编《佛教与历史文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23~149页。
[60] 《法苑珠林》卷88,《大正藏》卷53,926c。
[61] 董群《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学思想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72~73页。
[62] 见净源《原人论发微录》卷中、圆觉《原人论解》卷中。
[63] 1032~1033年
[64] 《镡津文集》卷1,《大正藏》卷52,649b。
[65] 《镡津文集》卷3,《大正藏》卷52,661b。
[66] 楠山春树《道教和儒教》,福井康顺等监修《道教》第2卷,朱越利、徐远和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48页。
[67] 楠山春树《道教和儒教》,福井康顺等监修《道教》第2卷,朱越利、徐远和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56~58页。
[68] 《无上秘要》卷46,《道藏》第25册第165页。
[69] 《太上老君戒经》,《道藏》第18册第204~205页。
[70] 鎌田茂雄《中国佛教通史》第4卷第204页。
[71] 尤其是戒律方面。
[72] 《高僧传》卷11,《大正藏》卷50,401c~402a。
[73] 415年
[74] 卿希泰《中国道教史》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增订本第406页。
[75] 《上清大洞真经》卷1,《道藏》第1册第516~518页。
[76] 《上清大洞真经》卷1,《道藏》第1册第516~518页。
[77] 《太上老君戒经》,《道藏》第18册第201页。
[78] 关于《玄妙内篇》,福井康顺先生认为是作于南朝初年(见其文《玄妙内篇□□□□》,《岩井博士古稀纪念典籍论集》第564页,东京,1963年),吉冈义丰先生认为它成书于430年前后(见《道教□佛教》第三第59页,国书刊行会,东京,1976年)。
[79] 谭蝉雪《敦煌道经题记综述》,《道教文化研究》第13期,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1版第23页。
方位
口吸之精
气色
形状
下布人身部位
东方
青阳之精
青气
木星
肝脏
南方
丹灵之精
赤气
火星
心脏
西方
金魂之精
白气
金星

肺脏
北方
玄曜之精
黑气
水星
肾脏
中央
高皇之精
黄气
土星
脾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