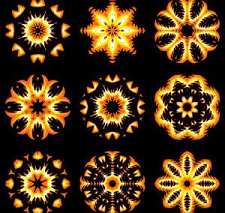禅者眼中的和谐社会
发布时间:2020-05-09 14:22:07作者:佛心网
内容提要:中国历史上所谓的民间宗教与正统宗教的冲突,涉及到“个人与社会”、“宗教与权力”的辩证关系。运用禅宗的缘起式思维方式,有助于形成多元的、和谐发展的社会与宗教的关系。
关 键 词:民间宗教正统宗教禅者缘起式思维方式
作 者:李向平,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中国宗教发展到宋代之后,出现了形式不一的宗教结社活动,而到了明代中叶,则出现了大量的民间教门。明代中叶之前,民间教派中的弥勒教、摩尼教与白莲教占主导地位,弥勒下生思想成为神灵信仰的体系中心;但自明代中叶至明末则出现了许多教派,他们在教义、组织、仪式等方面已经区别于原来的民间教派,以至于可以称之为“明清新兴民间宗教”[1]。
从佛教的发展来说,从正统佛教之中分化出民间佛教的时间是在南宋时代。南宋初年,浙江、江苏分别出现了两个弥托净土教派,即白云宗和白莲教,它们初为净业团体性质的佛教组织。而后来的弥勒教、大乘教,则是从中异化出现的民间佛教。这些宗教,曾经被人类学家称之为民间宗教(folk religion orpopular religion)。但是,这些宗教及其信仰方式一直被正统儒学以及正统宗教视为异端、非法的迷信,受到主流价值体系、支配性话语的打压而得不到正常的发展。因此,讨论中国历史上佛教发展的民间形式,对于理解中国宗教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发展关系,以及对于当前和谐社会的构建,将具有学术与现实的双重意义。
佛教发展的民间形式
中国古代的佛教寺僧,一般可以分为三大类:1、官僧,由国家拨款供养以负责完成皇家仪礼;2、私僧,由一些大户官宦提供食住;3、民僧,由一般信仰社群的微薄捐赠加以供养。与此相应,中国古代的佛教寺庙也分为官寺、私寺与民寺3种。
在早期的佛教史籍中,这3种寺庙是严格区分的。在这3种寺院机构之中,以国家资助作为后盾的官寺,其寺院经济一直最为雄厚。其次是由达官贵族所供养的私寺,其寺院经济虽然不敌官寺雄厚,却也颇有影响,往往能够长盛不衰。虽然中唐以后,随着门阀士族的衰落,私寺的寺院经济大幅度萎缩,但与一般民寺相比仍然雄踞于前。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只有民寺的寺院经济自始至终一直最弱,其寺院的兴废也最频繁。[2]
从宗教社会学意义上来讲,佛教的寺庙组织与其它宗教组织一样,不过是创造了一种新的人群集合模式、社群关系而已。乡村佛教组织的社会依托一般是乡村组织(乡村行政组织)、宗族组织(血缘祭祀组织)与乡里宗族组织,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各个组织的合一特性。村中的寺庙组织及其成员,往往是由一个村里具有或远或近血缘关系的亲戚所组成,因而这类佛教组织大都血缘型很强,但其职业的因素并不突出,相反宗教信仰与宗族制度的内在关系紧密。宗教信仰活动往往会体现着家族组织和乡族组织对于地方事务的控制,联系着信徒与乡族之间的相互关系,稳定地方秩序。[3]寺庙的修建甚至成为家族组织的分内事情,所以,佛教的寺庙或组织可以以家有、族有的形式而发展。这个发展趋势,时至宋明时代体现得越来越强烈。
宋至明清时代,中国社会动荡,宗教家辈出,民间教门层出不穷。一个神消失了,另一个神又出现了。特别是明中叶之后,佛教禅宗与阳明心学相互发明,使人的主观能力、心的悟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极大的扩张,以至于激活了民间造神的机制,将一个造乎天地、掀翻天地、赤手可缚龙蛇的精神心性膨胀为圣人神秘主义;借助于宗族、乡村组织的力量,自创新型宗教,试图圣化天下,再作天子;或者是自封为神,以此号召天下,形成新型的宗教崇拜。
尤其是主张禅净合流的佛教思想,提出一个“心”的概念,成为了当时乃至以后中国佛教宗派之间能够融通的基本范畴,并且开启了后世中国佛教多元发展的历史格局;它在宗教实践上强调“六度善行”,强调修持净土法门的仪轨和法式,适时地满足了当时民间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净土信仰的需求。所谓的三教合一,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得以呈现的;所谓的教出多门,也无不以此为基础。
明代中叶的民间教派,一是以罗教或无为教为代表,提倡自证本性,追求顿悟以证无生;另一种教派是以东大乘教、黄天道为代表,提倡内丹修炼,求得金丹以证无生。两大系统均奉“无声老母”为其信仰核心,而在无声老母之下,亦可信仰弥勒佛。[4]其中,作为中国佛教禅宗发展的民间形式,罗教将禅宗从文人士大夫的手里解放出来,以世俗的语言向社会底层传播,改变了中国佛教禅宗的历史发展格局。
罗教,亦称罗祖教、无为教,其创教师是罗梦鸿(1442-1572),或称罗孟洪,道号无为居士。罗教的核心思想就是禅宗教义。明清时代,它曾一度发展成为活跃于华北、江南、西北等十几个省份、首屈一指的民间大教派。
罗教以一种革新佛教的方式吸引社会大众,以禅宗的继承者自居,教义上则号称三教合一,老子、孔子与释迦并尊。它的宗教实践活动也和正统的佛教禅宗一样,强调成佛的方便:不需要出家,不需要朝山进香;世俗生活之中,即能够顿悟成佛、直入天宫。这些教义及其修持主张很受民众欢迎。同时,罗祖教还以其特有的“真空家乡”、“无生父母”、“自在天宫”等民间信仰的方式,宣讲佛教禅宗的教义。
罗教的典籍——五部六册,集中反映了这些思想特征。其文字通俗易懂,广泛采用流行于民间的俚语粗言,掺杂以五言、七言和十言韵文,朗朗上口,可唱可白,形同顺口溜,所以一旦刻印流行,立刻广受欢迎。如“……老祖师,为大众,不辞辛劳。一切人,今有缘,个个明心。想旷劫,遭流浪,轮回生死。今有缘,得正法,总报恩情。”[5]为此,明清两代,五部六册曾经一版再版,以更世俗、更简易的形式而风靡于社会下层,这不仅扩大了罗祖教的影响,而且对正统的佛教道教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所谓“山河大地为佛像”、“雷震太虚为法鼓”,所谓“佛祖大法本无边,临济宗派注先天,后代捧香来戒法,弟子替祖把道传”。这些无不表明罗祖教的社会影响已经超过了正统的佛教和道教。尽管其思想逻辑、信仰方式与正统禅宗基本一致,都不要求信众出家为僧,但是后者具有正当性,前者不具备正当性。
然而,罗祖教并不甘心自己的非正统地位,他们想方设法地想要获得正统特征。他们曾经设想将五部六册作为佛教的经典上奏皇帝,及皇帝册封罗组,“御制龙牌,助五部经文”等等,并试图将五部六册混编于大藏经之中。后世的罗祖教教徒亦曾附会皇权以获其正当性,同时在宫中权势太监和王公大臣的庇护之下,假传圣旨,以御制龙牌榜文为通行证,大量印行五部六册,发遍全国。[6]
虽然罗祖教从来没有获得正统的宗教正当性,但是它的五部六册却标志着中国民间佛教第一次构成教义体系,是民间宗教教义成为体系化的时代象征。从此,民间宝卷大量问世,几乎成为民间宗教经典的代称,民间宗教家如欲以宗教干预、动员社会,大多会以宝卷名目,而在官府当局则被视为“邪说”、“妖书”。自明代万历年间之后,官府就开始明令禁止一些宝卷的问世和流行。
民间宗教或民间佛教的非法特征
民间社会这个词汇,很容易使人想到水浒梁山等农民起义。在某种程度上,它总是象征或表示着一种与官府相对立、对抗的民间势力。而民间宗教也是如此,往往不是一种正统的宗教或宗教信仰。虽然民间宗教与儒家伦理常常具有一种相当协调的互动和渗透,然而正是这种互动的社会特征,造成了中国民间宗教无法摆脱的双重性。
一方面,“禁左道以正人心”,历来就是专制帝国的重要责任。国家代表了它所认可的精神信仰及其秩序,而交通鬼神与预示未来的种种异说或邪术,无不具备颠覆国家权力秩序的可能性,所以专制帝国不得不设计出一整套宗教制度以制约宗教活动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方式,并将服从国家权力秩序的宗教发展者视为正统。另一方面,中国历史上历代的农民起义,无不使用某个宗教信仰作为反对朝廷的价值符号以及动员民间社会力量的基本方式。所谓“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就是指处于权力底层的社会群体,要想成为历史变迁的主角,他不得不“为信仰而战”,为获得自己行动的合法性而斗争,直到最后成为一朝圣主、自居为天下正统。
相对于国家权力对于宗教、信仰的控制而言,一个僧人若要获得僧职,必须从属于某个“官寺”。他必须在某个官寺之中呆上很长一段时间才有可能获得一个僧职。没有僧职的和尚就是在俗僧人,对于权力秩序及其精神秩序来说,是一种潜在的威胁。特别是在晚期帝国时代,即使是僧人也不会从属于一个固定的寺庙,不会全部从事宗教礼仪活动并以此来排斥其它各种追求。他们是广义的佛教徒,居于佛门内外,并不是完全的佛教弟子。所以,中国社会之中的僧道与俗人之间的差别,远远没有西方僧侣与平民之间的差别那么明显。成千上万的游方僧道,已经成为煽动叛乱和从事法外活动的可悲温床,从而对国家权力构成了一种新的威胁。通过法令而实施的控制,只能对那些定居于一地并受当局管辖的僧道人员才有效力。[7]所谓的民间宗教或民间佛教恰好是处在这个权力秩序管辖的外围。
史书记载的民间宗教盛行的现象,大多涉及王朝秩序难以容纳这些脱离了权力秩序的宗教人士或社会群体。所以,“近日妖僧流道聚众谈经,……有一教名,便有一教主。愚夫愚妇转相煽惑。宁怯于公赋而乐于私会;宁薄于骨肉而厚于伙党;宁骈首以死而不敢违其教主之令。此在天下处处盛行,而畿辅为盛。不及令严而禁止,恐日新月盛,实烦有徒,张角、韩山童之祸将在今日。”[8]这里指出了封建王朝的忧虑往往开始于流动的宗教群体及其控制之外的宗教活动。
历代王朝大多主张,“严禁邪教,莫善于保甲”。[9]要将宗教活动置于国家世俗权力制度的安排之中,将权力秩序的稳定与这种精神价值秩序的稳定紧密联系起来,容不得其间有任何差错的出现。像白莲教、罗教这样的民间宗教,在官府看来,他们“蔓引株连,流传愈广,踪迹诡秘。北直隶、山东、河南颇众。值此凶年,实为隐忧”。[10]实际上,仅仅是因为人多和行迹诡秘,它们就已经招引了朝廷的无比担忧,难免成为非法的邪教了。
为此,《大明律》要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对此类“左道”、“邪教”的流行严加禁止。“凡师巫假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11]与此紧密联系的是,传统中国社会中的政治——道德冲突,往往不直接以权力的或经济的要求提出,相反常常以民间宗教的另一种天命信仰的形式提出。这就使传统中国社会底层群体的反抗行动,往往带有双重意义:一是要争取政治权力,二是要同时获取天命的自我证明,重坐天下。他们的起义,因此也是天命信仰的另一种表达形式,即“革命”行动——革其丧失了天命者的命,使天命再获人间正道的证明和落实。因此,中国宗教一般所具有的双重特性,在民间宗教那里是神权和族权的结合,在正统宗教那里则是权力与政治上的信仰特权的结合。它们二者之间的对立,必然就会导致各自的上层宗教领袖对掌握政权的欲望,而这种欲望常常要以两种形式出现,一种是投靠现政权,一种则表现为政治野心。[12]
在此两相对立的权力秩序之中,非统天下者即难免陷于非法的境域,非正统者即为旁门左道。宗教或佛教只能存在于国家权力秩序之中,方才具有合法的可能性。一旦出离了这个秩序架构,就极有可能陷于非法状态而被禁绝。
曾有外国学人认为,在中国具有公共性质的士人聚会,既没有出现在私人主导的宗祠祖庙里,也没有出现在国家主导的儒教寺庙里,相反出现在寺院这样一个媒介空间里。寺院经常作为士人的文化社交活动场所,很少是因为它的宗教信仰功能,而是因为其优雅别致和清净的环境。除此之外,寺院还被认为具有“公共空间”的特征。[13]然而,国家权力十分忌讳“在俗僧道”(secular clergy),所以寺院空间的“公共”特征总是十分有限。对于那些不入“僧录司”或“道录司”的僧道人员,国家总是设法要他们进入一定的管理组织,收编进入寺庙体制,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将这种管理方法使用到那些生活在平民社区的、广大民间宗教的职事人员身上。
所以,正统的佛教僧团组织更关注丛林制度及其精神修持,而对于佛教信徒的社会生活则一向不太注意。如果要对社会生活或权力秩序构成影响,那就是在民间佛教的形态之中,或者是在精神个体的佛教信仰已经集结成为权力秩序所难以容纳的程度,如在民寺或私寺的佛教形态基础上所构成的佛教结社或下层社会空间。
宗教间正统与异端的差异
实际上,在正统和异端之间并不存在着截然分宜的界限。不论就外部而言正统信仰与异端信仰之间存有着多大的不同,然而仔细考察就不难发现在它们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根本信仰。“异端通常声称是‘初创\’传统的继承者,而把正统派看作是偏离者,但这些偏离者并没有与原传统完全脱离关系;正统派通常声称异端派误解伪造了本思想的某一根本观点或命题。”[14]
正统与异端之间的界限,往往在于权力的认可与否,在于为权力秩序所认可的象征建构及其时间序列,至于信仰的内涵则是无所差异的,如果存在差异,那就是民间信仰大都是以民俗的形式进行崇拜,并不介入国家官方的祭典。所以,民间的信仰传统对于官方的正统信仰往往采取接受或者仇恨,或者干脆不理睬的态度。然而,无论是在社会的中心还是在权力的边缘,它们对于主导型的价值信仰并无刻意反对的意图,也没有改变这个主导传统的历史能力。民间宗教所致力的方向,仅仅是要由民间转为正统,以此获得政权所认可的正当性而已。
民间宗教、民间信仰往往被视为一种否定性的传统,实际上它既是一种反规范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传统,同时也是一种“立志消灭传统的肯定性传统”。[15]所谓“革命”——革其天命而另立天命的权力本质,在此层面上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天命获取者即为正统、正当,丧失天命者随即就沦落为异端、服从者。它们并不消灭传统,只是需要一个为自己所能利用的传统。因此,正统与异端的差异,仅仅在于政权的认可与否。
正统的佛教即存在于官寺之中的佛教及其活动,但是在民间宗教的发展过程之中,那些私寺和民寺则与民间宗教混为一体。此外,民间宗教的一些活动也会获得僧道的响应和配合。而在民间教门之中,借助于寺庙诵经做会者也不在少数,至于民间宗教与正统佛教道教拥有共同的宗教节日,一道参与庙会的也不少见;即使是邪教案发,也由于民间宗教与僧道的密切关系,寺庙还成为民间宗教当然的避难所,为它的活动者和经书予以保护和收藏。所以,寺庙在民间宗教的运动之中也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它们不仅是乡村社会传统信仰的中心,同时也是民间宗教与乡村僧道巫合流的重要空间场所。[16]
至于在俗僧道,仅仅是因为妄称教主、自传教义,就被蒙上了不受宗教纪律的约束、不服从国家的控制管辖的罪名。而国家权力机构之所以要以度牒制度管理僧道人员,就是因为社会上还存在着这样一批不受国家权力控制的礼仪职事人员,其目的是为了使“无赖之徒不得串入其中,以为佛老之砧”。朝廷甚至会下诏禁止在俗僧道、禁止“应付僧”的出现和扩大。
此外,宗教之所以会有非正统的发展形式或被称为邪教①,除了来自权力秩序的不认可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宗教内部的利益或信仰方式之间的冲突,以及对于教义解释方法的冲突,导致了宗教间的正统与异端的区别。比如,罗教批判正统佛教的繁琐礼仪,公然以正统佛教自居,其信徒可以娶妻生子、在家修行,所以深得大众和下层百姓的信奉。然其在佛门则是一派排斥之声,正统佛教对此尤感震惊。名僧憨山德清在山东的时候,见佛教信徒几乎尊信罗教而不知佛教三宝感到十分震惊,以为外道盛行。莲池袾宏也对此极力拒斥,以为其“假正助邪,逛吓聋瞽。凡我释子,宜力攘之。”[17]
缘于此,佛教界的名僧大德者一方面着书立说,奔走摄化,辨伪正讹,以达到破邪立正之目的;另一方面,则发起和主持编撰、刻印新的《大藏经》,颁行全国,借此以正压邪。[18]佛教界的着名高僧如紫柏真可、憨山德清和密藏道开等等,都曾带头批判罗祖教的异端行径。
这些言语与行动,与官方对于罗教的态度几乎一致。虽然官府的出发点与佛教界相异,但是基本方法却是惊人的一致。如“南京礼部伪毁邪教以正风俗事。照得无为教惑世诬民,原系大明律所禁,屡经部科奏准严杜。……刊刻五部六册等板,夤缘混入大藏,……”云云。[19]因此,不难看出,权力甄别以及宗教派别内部的正统与异端的区别,是中国历史上正统宗教与旁门、左道得以构成的两大基本要素。
正因如此,正统的、中心的信仰方式与边缘的、旁邪的信仰方式常常存在着冲突,特别是对宗教中心地带的批判会来自于宗教边缘地带。民间宗教就处于这种边缘地带。尽管这种批判从来也没有获得成功,但是它们却一直存在着,一而再再而三地复活,断断续续、极不稳定地存在,并且在多次复兴之后重又回归到一个价值源泉上来——争取发展的正当性。
禅者的世界:透明的差异
实际上,中国历史上的宗教在所谓“正”与“邪”的冲突问题上,不仅仅涉及政教关系,更是涉及到“个人与社会”、“宗教与权力”的辨证关系。日常生活世界之所以能够沟通,是因为所谓的“视野相互性”或“立场的互换可能性”。宗教间正邪关系的构成与冲突,大抵上则是因为这种视野与立场的缺乏。
然而,禅宗的世界即使存在差异,它也应当是一种透明的差异。a是a的同时,又是b,又是c;但它不是b,也不是c,事实上还是a。在它们之间,并非没有差异,但其差异是透明的差异,是没有其它外在因素渗透的差异。[20]
与西方宗教或西方哲学的因果式思维方式不同,中国佛教、禅宗的缘起式思维方式则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带着与一切事物的关联性而形成的,因此事物无中心地、超越中心地形成于横竖无尽的相互关系网络之中。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中心,可以把一切都看作是世界的中心。因果式关系走向一神教,缘起式关系则走向承认八百万尊神的多神教,所谓的事事无碍法界。
这就意味着一切事物总是同时地、整体地形成,仅仅依靠自己无法存在的事物在依靠自己以外的一切事物的同时,即把其他一切事物作为“缘”而发生于存在世界。所以,一切事物存在的本质都是无自性的,即一切事物只有存在于整体的关联之中它才能存在。存在就是关系本身。一个事物a只有在与其它一切事物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中才能成为a这个事物,这就是说,在a的内部结构中自身以隐蔽的方式无一遗漏地包含了其它一切事物,从而在一个事物的存在中也有整个宇宙的参与。存在的世界,如此这般地、一瞬一瞬地、崭新地形成下去。一一微尘中,见一切法界。[21]
正邪之间的强烈区别,正好是这种关系的绝对化产物。本来是一种多元的、多种关联的宗教发展形式,最后只能是一种发展形式;本来是无中心的关联,最后则走向自我中心、权力中心。更加严重的是这种种关系,无一不是要寻找一种权力庇护,最终构成一个权力中心,从而败坏了无中心、无因果的事事无碍法界,形成一种权力的庇护关系主义。
真正的无中心关联,应当是一种公共性的关联。所谓的自明性、公共性、相互主观性、反复性,应当体现为各种宗教群体、社会团体均能在其中表达自己的信仰、利益的依托。只要舍去这层权力庇护关系,由禅宗的无中心的关系,就有可能构成多元、透明、多层次的社会、宗教关系。
如果说,在中国宗教的发展史之中,存在就是关系,继而是关系决定信仰、关系决定正邪的话,那么,这种种关系及其处理,应当逐步地发展成为一种独立于权力之外的变量,并且成为今后中国宗教、宗教与社会、宗教与权力等等关系的正当化、规范化、法制化的基本关系。
注释:
① 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教之所谓“正”与“邪”的标准,即以朝廷官府和正宗宗教组织的认可与否为标准,认可者为正,否则为邪;现代社会之所谓邪教,其判断准则应当为是否利用宗教而损害他人生命和财产,是基于相关法律的标准。
参考文献:
[1]郑志明. 无声老母信仰渊源. 第一章导论. 台湾文史出版社,1985
[2]段玉明. 中国寺庙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320-321 [3]陈支平. 明清福建的民间宗教信仰与乡族组织. 厦门大学学报,1991(1)
[4]路遥. 山东民间秘密教门.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37
[5][6][12][18]马西沙、韩秉方. 中国民间宗教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6-9、173、250、567-568、185
[7]孔飞力.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上海三联书店,1999:52、56

[8]神宗实录.(卷五三三). 万历四十三年六月
[9]黄育梗. 破邪详辨卷三. 清史资料(第三辑). 中华书局,1982:60、62
[10]神宗实录.(卷一八二). 万历十五年正月
[11]大明律.(卷十一)
[13]timothy brook. praying for power:buddh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gentry society in late-ming china.harvad university press,1993:114
[14][15]爱德华·希尔斯. 论传统.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357、315
[16]梁景之. 清代民间宗教与乡土社会. 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290-294
[17]莲池大师全集·正讹集
[19]南宫署牍(卷四)
[20][21]青井和夫. 社会学原理. 华夏出版社,2002:170、167-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