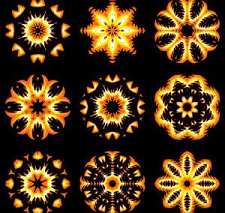富那夜奢与付法传承
发布时间:2020-04-29 15:18:13作者:佛心网富那夜奢与付法传承
富那夜奢,又作富那奢,为禅宗西土传承中的一个重要人物,然而他前有胁尊者,后有马鸣,因此他的光芒却被影响更大的老师与弟子掩盖了,成了两颗巨星之间的点缀,有此师,有此徒,亦是难得之缘,幸与不幸,孰能断之。
正是由于他成了两个巨人之间的中间环节,以至于他的光彩暗淡下来,乃至连他的存在在后世也成了问题。鸠摩罗什编译《马鸣菩萨传》,干脆将马鸣直承胁尊者,将富那夜奢一笔勾销。也许是由于受到罗什的影响,僧 《萨部多记》以胁尊者为第十,马鸣为第十一,又录《长安城内齐公寺萨婆多部佛大跋陀罗师宗相承略传》,以勒比丘(胁尊者)为第八,马鸣为第九,富那夜奢的名字同样不见了,而胁尊者与马鸣相连,似乎也认可或印证了马鸣为胁尊者直传弟子的说法。
据《传法藏传》,富那奢(富那夜奢)为第十代,是胁尊者的直传弟子,也是马鸣的亲教师,然此书一向被认为是昙曜编著,不受重视。在禅宗史料中,富那夜奢为第十一代,上承胁尊者,下传马鸣,此说又被认为是禅宗的编造,更不为后世学者所接受。
那么究竟富那夜奢是后人编造出来的人物还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呢?
中国学者大多相信鸠摩罗什之说,以为他所译的《马鸣菩萨传》是时代较早、又比较原始的材料,因此应当是可信的。其实马鸣在佛教史上的地位,在中国首先是由罗什及其门下抬起来的(1)。罗什不仅译有马鸣的《大庄严论经》,还编译他的传记和禅法,并将属于有部及譬喻师的马鸣塑造成大乘佛教的先驱,其弟子僧 于《大智释论序》中将马鸣与龙树并列,以为微二人,则佛法"沦胥溺丧",二人"可谓功格十地,道侔补处(即将成佛的菩萨)者矣"。正是由此,马鸣才被尊为大乘佛教的先驱,才有后世《大乘起信论》为马鸣之作之说。由于罗什及其门下对马鸣的宣扬,后人便认为他对马鸣的思想历史了解很多,也就接受了他关于马鸣的史说。
马鸣为胁尊者直承弟子的说法是否可信呢?马鸣的时代,诸说差别不是太大,一般认为他是佛灭后五百年时人,也有说为佛灭后六百年时人,总之,一般认为他活动于公元一世纪。僧 说他起于正法之末,即为五百年时人。而胁尊者的时代则难以确定,但都认为他是有部早期的领袖,其时代早于马鸣。胁尊者被认为与迦王一世同时,而且当时他已在晚年,应该说稍早于迦王一世。而马鸣应该是迦王一世之后的人物,马鸣的《大庄严论经》卷三、卷六两次提到迦王,并说"我昔曾闻",可见马鸣的时代迦王一世已经是过去的历史人物,大概他并未见过迦王,所以更没有可能成为胁尊者的亲传弟子。
据《马鸣菩萨传》,马鸣为中天竺华氏国人,时北天竺小月氏王伐中天竺,索要三亿金钱以为赔偿,华氏国王以佛钵、马鸣、慈心鸡当之。据羽溪了谛在《西域之佛教》中考证,这位月氏王应当是丘就却,而丘就却为约于公元40年至75年间当国的贵霜王朝之第一代统治者,马鸣与其同时,则和与迦王一世同时的胁尊者难以谋面,因为迦王一世约于纪元前58年至前31年当国,和丘就却差了百年(2)。
既然胁尊者和马鸣相距甚远,不可能是直承关系,那么《付法藏传》和禅宗史料所载的在二人之间有富那夜奢作为中间环节的说法就有可能是正确的,而且在《大庄严论经》中有明确的证据。《大庄严论经》为马鸣之作本为定论,但是由于二十世纪初德国学者勒柯克在新疆库车发现了梵文写本残卷,内容与《大庄严论经》相同,然其跋文却说是童受作,这就引起了疑问。德国学者吕德斯据此认为作者应为童受,法国学者莱维则驳斥了吕德斯的观点,认为《大庄严论经》的作者还应该是马鸣,此写本不过是马鸣原作的改写本(3)。莱维的说法应当是站得住脚的,童受稍后于马鸣,有可能是马鸣的同门,其改作马鸣之作当不为怪。《大庄严论经》卷首云:
前礼最胜尊,离欲迈三有。亦敬一切智,甘露微妙法。并及八辈众,无垢清净僧。富那胁比丘,弥织诸论师,萨婆室婆众,牛王正道者,是等诸论师,我等皆敬顺。我今当次说,显示庄严论。闻者得满足,众善从是生。可归不可归,可供不可供,于中善恶相,宜应分别说。
这段话先敬三宝,中述师承,后述造论旨趣,最关键的是中述师承之句。"富那胁比丘,弥织诸论师",显然用的是倒叙,先说其师富那夜奢,后说祖师胁比丘,再说远祖弥织(弥遮迦)等。富那夜奢的名字赫然在目,并且明确宣布他是作者马鸣、也许还是童受的亲教师,这么一来,马鸣的师承就非常清楚了。马鸣对于有部(萨婆室婆)、犊子部(牛王正道)同样尊重,表明有部与犊子部确实关系密切。
据此,在胁尊者与马鸣之间存在富那夜奢是毫无疑问的。或谓《大庄严论经》但有略称,"富那"未必是指富那夜奢,也就是说对富那夜奢的存在还有怀疑,那么《大毗婆沙论》能够帮助解决这一疑问。
据北凉所译《大毗婆沙论》卷十三杂 度入品第三上,"尊者富那奢重明此义,若无明、行在现在,当知十支在未来,八在次生中,谓识乃至有,二在第三生,谓生、老死。若生、老死现在,前十支在过去,八支在次前生中,谓识乃至有,二在前第三生,谓谓无明、行。若八现在,前二在过去,谓无明、行,二在未来,谓生、老死。",下页又有"以是事故,尊者富那奢所说义,全为明了"之句(4)。此品是专门讨论十二因缘(十二入)的,有部之说,或以无明、行为过去法,中间八支为现在法,生、老死二支为未来法,富那夜奢之说,解释更为灵活深入,他一方面仍然将十二支分为二、八、二三个部分,一方面又不将其固定为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而是认为三部分都可以作为现在世,他也不再局限于三世的模式,认为也可分为现在、未来或过去、现在二支,只是在未来和过去中保留了第二生、第三生之说,并未完全放弃以往三生的框架。《大毗沙论》显然是赞同富那夜奢之说,将之作为权威的解释的。此品还引了胁尊者的解释,从侧面反映了富那夜奢与胁尊者的关系。

如果说此处还不能清楚地表明胁尊者与富那夜奢的关系的话,卷三十九言六入与六触入体用关系时就足见证了,其言"尊者波奢(胁尊者)说曰:体是六入,若为触作依,名六触入,如钵体性是钵,比丘用故,名比丘钵。尊者富那奢说曰:体性入是六入,所作入是六触入,犹如铁钵,体性是钵,以盛苏故,名盛苏铁钵"(5)。此处先引胁尊者言,后引富那奢说,而二人的观点又是基本一致的,足见二人的师承关系。此处讨论的依然是与十二因缘有关的问题,六入为人之器官,一旦与外界发生接触,便由本然自在之六入变成了有触觉、认识之用的六触入,故六入为体,由有触之用变成了六触入,六入为触之依,无六入便无由有触。胁尊者强调六入为体,为性,为本,为依,触为用,为相,为末,为依他起,六入由触变成六触入,正如钵本体是体,因为比丘所用,便叫做比丘钵。富那夜奢的观点与胁尊者一致而又有所发展,他将六入称为体性入,六触入称为所作入,意义更加清楚,同以钵为喻,胁尊者讲的是比丘用,即钵为他而用,富那夜奢则说钵能盛酥,即钵本身的作用,这就更加深入了。
由此可知,在编撰《大毗婆沙论》时,富那夜奢已经成为当时的学术权威,被称为"尊者",他的观点也被视为权威的看法。但全书他的名字出现次数不是很多,出现最多的是胁尊者与四大论师,这表明他的地位还不能与前辈诸贤圣相比,可能他还处在中年。或谓马鸣曾参与《大毗婆沙论》的编订,然学界多将其作为此书编订后的人物,总之,在书中出现的富那奢在马鸣之前,可以认定就是作为马鸣之师的富那夜奢。
在最原始的史料中看不到对富那夜奢经历的描述,最早的记载见于《付法藏传》。据《付法藏传》卷五,胁尊者垂当灭度,令富那奢守护教法,富那奢唯然受教,"于是演畅微妙胜法",化度无量众生,其后于林中静坐禅修,时大士马鸣心怀骄慢,"计实有我甚自贡高",闻富那奢"智慧深邃多闻博达,言诸法空无人无我",便至富那奢所欲加摧伏,富那奢告以世俗、胜义二谛皆属空寂,世谛但有假名,第一义谛悉皆空寂,本来无我,有何可摧,马鸣初尚不解,后终折服,欲斩舌以谢,富那奢便止之,收其为弟子,又现神通,令暗室光明,使马鸣完全归服。富那奢入灭后,四众感念,为之起塔供养。
这一记载虽然较详,可信度却不高。马鸣成了有宗的代表,富那奢则成了空宗的代表。或因马鸣尊重"牛王正道",便将其塑造成犊子部"计实有我"的代言人,然将有部大师富那奢说成宣扬诸法本来空寂、皆不可得之义者,恐怕根据不足。依《异部宗轮论》及真谛、吉藏之释,说假部最早提出世谛、真谛二谛说(6),说假部成立于佛灭二百年中,在富那夜奢之前,然其说以世法为假,出世法为真,并无"第一义谛悉皆空寂"之义。言世法因缘和合,假名无实,本是佛法根本正理,富那夜奢持此义本不为奇,而言第一义谛亦属空寂为龙树之后之说,亦与有部正理相违,不可能是富那夜奢所持。因此这段记载中只有富那奢为马鸣之师是可信的,其他铺延实出于后人的编造,不足取信。
《付法藏传》固有编造,《马鸣菩萨传》更不可信。罗什所译以马鸣为胁尊者直传弟子,道是胁尊者以神通力,从北天竺至中天竺,欲收服辨才无碍的外道才俊马鸣,二人辩论,胁尊者先立"当令天下泰平,大王长寿,国土丰乐,无诸灾患"之论,马鸣顿时哑口无言,不敢破斥。胁尊者显然是用巧,因为这些美好的祝愿虽然只是虚幻的理想,马鸣却无法加以破斥,否则便会受到政治上的打击。因此马鸣口服心不服,后来胁尊者又显示神通,令马鸣折服。这一故事显然是罗什所闻的一种传说,因为前文已述,马鸣不可能是胁尊者的弟子。这表明罗什得之于传闻的东西不少,他关于马鸣、龙树、提婆等传不能被视为可靠的原始资料。
富那夜奢的经历思想传至后世者甚微,但他作为一代持法者的地位是不容怀疑的,这也表明《付法藏经》及禅宗史料并非全属编造,其中有史可徵的地方不在少数,不论是赞同还是否定其说,都须认真考辨,切不可不加思索地认定为编造。
注释:
(1)吕 《中国佛学源流略讲》94至95页,中华书局1979年。
(2)徐文明《迦腻色伽与大月氏王系》。
(3)季羡林《大唐西域记校注》988页注(二),中华书局1985。
(4)大正藏二十八册97页及99页。
(5)大正藏二十八册386页。
(6)渥德尔《印度佛教史》254页,王世安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