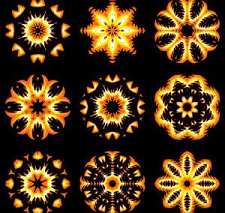第一章 我的生命被颠覆了
发布时间:2020-03-31 10:22:50作者:佛心网第一章 我的生命被颠覆了
第一次见到凯瑟琳时,她穿着一件很好看的深红色时装,在候诊室里紧张地翻着杂志。在此之前的20分钟,她在精神科外面的走廊来回踱步,说服自己依约赴诊而不逃走。
我到候诊室招呼她,和她握手。她的手又湿又冷,证明了方才的焦虑。事实上,虽然有两个她信任的医生大力推荐,但她还是花了两个月时间才鼓足勇气来看我。
凯瑟琳是个外表十分有吸引力的女子,中等长度的金发,淡褐色的眼睛。那时,她在我任精神科主任的同一家医院的实验室里做化验员,并兼做泳装模特儿赚外快。
我领她进诊疗室,穿过躺椅来到一张靠背皮椅前。我们隔着一张半圆办公桌对坐。凯瑟琳向后靠在椅背上,沉默着,不知该从何说起。我等着,希望由她来选择话题。但几分钟后,我开始询问她的过去。第一次会面,我即试图理清她是谁、为什么来看我这些问题的头绪。
在回答中,凯瑟琳逐渐向我透露了她的生平。她生长在麻省小镇一个保守的天主教家庭中,排行老二。哥哥比她大3岁,擅长运动,在家中享有她所没有的自由。妹妹则是父母最钟爱的孩子。
当我们谈到她的症状时,凯瑟琳明显变得焦虑而紧张。她说话很快,身子前倾,把手肘靠在桌上。她一直都为恐惧所扰。她怕水、怕卡到喉咙,怕到连药丸都不敢吞的地步;怕坐飞机、怕黑,更怕死这个念头。近来,她的恐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为了得到安全感,她常睡在大得够一人躺下的衣橱里,每晚要经过两三个小时的辗转反侧才能入睡。虽是睡了,但睡不熟,总是断断续续,很容易被惊醒。小时候常犯的梦游和做噩梦的症状也复发了,当这些恐惧和症状愈来愈困扰她时,她的情绪也就愈加沮丧。
凯瑟琳陈述这些经过时,我看得出她受的折磨有多深。多年来,我帮助过不少像她这样的病人克服恐惧的威胁,也很有信心能帮凯瑟琳渡过难关。因此,我打算让她从童年谈起,找出问题的根源。通常,这种洞察可以使人减轻焦虑。如果有必要,她的吞咽不那么困难的话,我会给她服一些抗焦虑的药,使她舒服一点。这是教科书上对凯瑟琳此类症状的标准处置。曾经我也从不迟疑地就给病人开安眠药,甚或抗忧郁剂,但现在我尽量少用了,要开也只开短期的。因为没有什么药能对这些症状的病根有所帮助,凯瑟琳和其他类似的病人证明了这一点。现在我知道必定有根治的方法,而不只是把症状压下去。
第一次会面中,我尽量不着痕迹地把话题往她的童年推。由于凯瑟琳对童年的事记得的出奇得少,我考虑用催眠来追踪。她记不得童年有任何大的心灵创伤,足以造成今日的恐惧。
当她竭力去回想时,才能忆起一些零碎的片断。5岁时,有人把她从跳板推到游泳池里,使她吓得魂飞魄散。不过她说,即使在那个事件之前,她在水里也从来没有舒服过。11岁时,她母亲突然变得很沮丧,无法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去看心理医生的结果,是接受了电击治疗,这些治疗使她母亲几乎丧失记忆。这个经验吓坏了凯瑟琳,不过,随着母亲病情的好转,逐渐恢复自我,她的恐惧也消散了。她父亲有长期酗酒的恶习,有时凯瑟琳的哥哥得去酒吧寻回烂醉如泥的父亲。酗酒也使他常对妻子动粗,于是她母亲变得更加阴郁退缩。但是,凯瑟琳只把这些事当做无可奈何的家庭纷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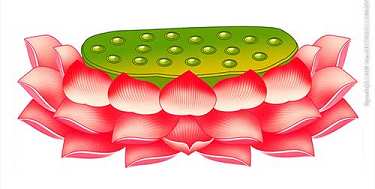
外面的世界情况好些。她在高中开始约会,她很容易和朋友打成一片,其中大多数是认识多年的伙伴。不过,她发现自己很难相信别人,尤其是自己小圈子以外的人。
她的宗教观念单纯而没有疑义。从小就被灌输传统天主教义理和习俗,她从来没有真正质疑过它的可信度和有效性。她相信一个恪守教义和礼俗的好天主教徒,死后将得到上天堂的赏赐;否则,将会遭受地狱之苦,掌握权柄的上帝和他的独子会做最后的审判。
我后来知道凯瑟琳并不相信轮回——事实上,她很少接触印度教的东西,根本不清楚这个观念。轮回是和她从小被灌输的观念完全相反的东西。她也从来没读过有关超自然或玄秘世界的小说,因为没兴趣。她安全地活在信仰中。
高中毕业之后,凯瑟琳修完了一个二年制的专业课程,成为实验室化验员。由于有了专长,又受到哥哥搬到佛罗里达州坦帕地(Tampa)的鼓励,于是她在迈阿密大学医学院的附属教学医院找了一份工作,在1974年春天,21岁时搬到迈阿密。
和大城市比较起来,以往的小镇生活虽容易、单纯些,但凯瑟琳庆幸自己逃离了家庭问题。
她在迈阿密的第一年,便认识了史都华——已婚,是个犹太人,并有两个小孩,但和她以前交往过的任何男孩子都不同。他是个成功的医生,魁梧而带侵略性。他们之间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化学作用”,但这段婚外情走得坎坷而崎岖。他的某些特质深深吸引着她,使她无法自拔。凯瑟琳开始做治疗时,她和史都华的关系已到第六年,虽然时有争吵,但感情仍是鲜活的。凯瑟琳对他的谎言和操纵怒不可遏,但仍然离不开他。
来看我前几个月,凯瑟琳动手术切除了声带上的一个良性瘤。手术前她就忧心忡忡,动完手术在病房醒过来时,她更吓坏了。医护人员花了几小时才使她平静下来。出院后,她去找爱德华?普尔大夫,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小儿科医生,凯瑟琳工作时认识的。他们一见如故,很快就建立起友谊。凯瑟琳可以对他畅所欲言,包括她的恐惧、和史都华的关系,以及愈来愈失控的焦虑等。他坚持要她来看我,而且不是别的心理医生——就只是我。爱德华打电话告诉我这回事时还强调,虽然别的心理医生也训练有素,但他认为只有我能充分了解凯瑟琳。不过,凯瑟琳并没有打电话来。
8个星期过去了,繁忙的精神科主任职务,使我很快忘了爱德华那个电话。凯瑟琳的症状却愈来愈严重。外科主任法兰克?艾可医生几年前就认识凯瑟琳,偶尔在实验室碰面时他们还会开开玩笑,他注意到了她近来的不快乐和紧张,有几次想跟她谈谈,但都半途打住了。一天下午,法兰克开车到一家小医院去演讲,在路上,他巧遇正开车回家的凯瑟琳。把她招到路边后,法兰克从车窗里大叫:“我要你马上去看魏斯医生,别再拖了!”
凯瑟琳的焦虑和痛苦愈来愈频繁,而且每次发作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她开始做两个重复的噩梦。其一,她开车经过一座正崩塌的桥,车子掉进水里,她出不来,快要淹死了。第二个梦是她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房间里,不断被绊倒,可是找不到出路。最后,她终于来看我了。
第一次见到凯瑟琳时,我完全不知道桌子对面这个饱受惊吓而困惑的病人,会把我的生活搅得天翻地覆,并且让我整个人也从此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