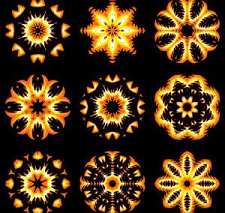唐初三阶教大德惠恭行历及其佛学思想
发布时间:2020-04-18 08:45:51作者:佛心网唐初三阶教大德惠恭行历及其佛学思想
——《法门惠恭大德之碑》考释
关于法门寺,当代学者康寄遥在《陕西佛寺纪略》中言:“西安附近各祖宝塔,对于法门寺塔,犹如众星之拱北辰。”何以言之?因为此中有如来真身舍利。由于法门寺独与佛骨相连,因此使之成为超越所有佛寺的佛教圣地。有唐一代,更是掀起了奉迎佛骨的狂潮,1987年,法门寺塔下地宫文物的出土,引起了世人的注目。这批文物中,有一方残碑,名《法门惠恭大德之碑》,碑文已发表三次[①],然均因录文及句读失误颇多,未能引起学界注意。近来重读碑文,发现惠恭乃是一位三阶教僧人。三阶教命运多舛,历遭禁断,经典、史籍存世者几稀,故此碑当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或当有补于我们认识唐初三阶教的传播情形和思想变化。兹将碑文重录并断句于后,进而试为阐释惠恭大德行历及其佛学思想。
一、碑文
此碑本镶于法寺塔基地宫之石壁中,出土时已断为数截。经拼对,此碑残高约1.60米,残宽0.64米,厚0.23米。碑首篆额两行,字有残损,每行现有三字:“□门惠恭△□德之碑”。碑文正书间有行体,残存30行,满行54字。碑阴铭刻《佛遗教经》,经校对知其为鸠摩罗什译本。现将重新整理的碑文录载于后,“△”符号表示其行隔,意补的字加〔〕表示:
〔法〕门惠恭〔大〕德之碑
(前缺五十字)为如来下△(缺43字)者也。法门寺者,本名阿育王△〔寺〕。(缺14字)初生魔焰,正□百年,斯主出代,用人□□□□。赢正指位,□天于之□癸,乃人同巨历造生地狱诽谤△(缺11字)仍起心花于镬汤,恶王归依,清业林于信圃。遂发愿营塔,遍四天下,精心入道,释梵光,其福田至感精微,鬼神尽△(缺9字)神光夜明,八万四千,不日而就。其寺则育王之一所也,因而为号。惠恭禅师之上居焉。
禅师俗姓韦氏,本鲁国邹人。其△□□□□□□□□□邑天祚归商,以豕韦称霸,盖得姓于其国,因而命氏。禅师虚而保真,清而容物,感阴阳之粹气,得天地之淳风,思越断常△,□□□□□□□□不染嚣尘,髫龄之年已堕僧数。岂非善吉罗汉自罄家资,玄鹦比丘先摧论鼓。年甫十四,依慈门寺道场审禅师听受三△[阶][佛][法],□□□□句,心远七憎,以果收因,则含生皆佛;将时验质,则以位独凡。上根下根,洞悟其旨,真学妄学,究竟其门。苦行精诚,年逾十载。△□□□□□□□□禅师者,佛法之机衡,幽途之炬烛。心滋有待,智入无端,名称普闻,众所知识。禅师稽首接足,亲承问道,摄念归依,习禅三△〔载〕。□□□□□□□会真空。虽业利已修,化迷入悟,禅师慈愍有待,将击群蒙,乃阴照昏山,明发心海,解体三昧,利周四衢。年廿三,还居此寺。△□□□□□□□□□花,戒珠圆明,能清五浊之水。上士稽首,中庸归命,意消神悟,目击道存。以为定慧不兼,静乱殊学,遵行五众,虔奉四依。△□□□□□□□杨之□。惠日明代,非开寂灭之域,遂别安禅院,清净住持,夙夜翘诚,供养灵塔。贞观之末,沐浴舍利。便烧二指,发菩提心。即△□□□□□□□,清净大众,宛如初会。倏睹尊仪,情如新灭。岂止灵光浮景,空惊迦叶之心;宝相澄辉,似入阇王之梦。[②]△
□□□□□□之道,行戒言之放心[③]。△天皇□□,□□地络,克振天维,安上□□,定礼制乐。以为垂衣端拱,得尊之于此方;御升乘乾,非超之于彼岸。悬般若之镜,圆照十方;燃涅槃△之香,上□□□,□报先于施作;旷劫之强,缘道始于檀为。大千之化主,显庆首年施绢三千匹,修营塔庙[④],△敕师结□□讫冥,因假愿力以庄严,若神功之再运;感灵仪而示现,如轮王之重修。禅师清净其心,深信坚固,集众法宝,如海导师。尝与胜光△寺惠乘〔法〕〔师〕同德比义,赠禅师行瑭布巾,表为善友。则知舍利、迦叶更为显扬,文殊、普贤乐相诚仰。俄而乘师下代,德音绵邈,道林存化,虔之△独存。长□□煜,耻为孤照昏衢,智眼恨不兼明,悔叹业像奔驰,将沦教戒;爱马腾跃,先亡苦空。故勒石题经,昭其未悟。敬镌《遗教经》、《般若心经》△各一部。□□□道,我执断灭,明性起于禅枝;法空见前,引尸罗于智果。顿渐宗印,终始住持。寂静律仪,则睹文齐相;澄清等忍,则观义忘言。故△知;道存□□,□执油于副墨;理归微渐,见法雨于临墀;四果声闻,感无涯而丧偶;十方菩萨,睹即色而归心。宁止香艳,成云发东方之紫气;花△缨结雾,□□□之青光而已哉!当愿:定镜流辉,尘清四念;心珠凝彩,照引三明;芥城几空,海印无底;河神屡陨,法母常安。弟子学谢文圆,才非△武库,有□□□,期种觉于雷阴;未获归依,冀前缘于智胜;德山高远,思三昧于瞻□;定域幽深,心不及于疑始。希为善诱,敢作铭曰:[⑤]△
识海波□,□□扇激。非我法王,谁救沦溺。般若实性,尸罗妙迹。化城屡迁,真空不□。其一。
十方诸佛,从法立名。相有始终,心无坏成。惠空七觉△,境智□□,□□度者,实无众生。其二。
世间实有,名为一合。智越断常,心超间塔。种觉□映,一多相纳。怨形妄心,显见灵塔。其三。
正像既迁,二阶△无实。□□□□,四依挺出,了别爱憎,弘扬诫律。重振法鼓,再明佛日。其四。
心相不〔二〕,国土皆空,虽含觉性,不废愚蒙。始明惠炬,终扬戒风。希除△妄识,□□□□。其五。
碑若天工,字凝神运。密严显迹,含性招训。降伏四魔,归依百部。定水澄影,迷津息问。其六。
佛前佛后,劫尽劫生。[⑥]尘界虽暗,法△眼恒□。□□□果,包含色声。惠空无际,福尽有情。
永昌元年岁次乙丑□月庚戌朔卅日已卯
法门寺僧惠恭树
郭□□一心供养
二、惠恭禅师生平考证
法门寺惠恭之名,不见于现存僧传。出土之碑亦未载其生卒年份。然而,据碑载惠恭禅师“年廿三,还居此寺”及“贞观之末,沐浴舍利”推断,其于贞观二十一年前当已至法门寺。另外,从其在贞观年间于法门寺的弘法成效看,至少需近十年方可成就,故由此可再行将其至法门寺的年限上推约十年。这可作为其下限。参之于其它证据,惠恭住在法门寺肯定不会早于贞观五年(631年)。原因有二:一是法门寺本身的情形;二是碑文中提到的惠乘法师之行历。
法门寺,隋之前名阿育王寺,隋代名为成实寺。唐武德元年(618年)唐高祖李渊在称帝前数日于隋大丞相任上,下令改之为法门寺。不过,贞观五年前的法门寺仍呈败落之状,于关中佛教影响有限。据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载:“及周灭法,廂宇外級,唯有两堂独存。”[⑦]“大业末年四方贼起,诸乡在平原上,无以自安。乃共筑此城,以防外寇。唐初杂住,未得出居,延火焚之,一切都尽。二堂余烬,燋黑尚存。贞观五年,岐州刺史张亮素有信向,来寺礼拜,但见古基曾无上覆,奏敕望云宫殿以盖塔基,下诏许之。”[⑧]因构塔上尊严相显。张亮又报请太宗批准,将塔基下佛骨请出以示众,引起包括京师长安在内的周边僧俗的普遍信奉,“无数千人一时同观”[⑨],场面颇为盛大。由此,法门寺于关中塔庙中脱颖而出,声名远播。惠恭禅师可能是因此缘由而移住法门寺的。
此碑又载,惠恭禅师“尝与胜光寺惠乘法师同德比义,赠禅师行瑭布巾,表为善友”,“俄而乘师下代”云云。惠乘,也作“慧乘”,《续高僧传》卷二十四有传,其文曰:
释慧乘,俗姓刘氏,徐州彭城人也。……叔祖智强,少出家;陈,任广陵大僧正,善闲《成论》及《大涅槃》。乘年十二,发心入道,仍事强为师,服膺论席。……大业六年,有敕郡别简三大德入东都,于四方馆仁王行道,别敕乘为大讲主。……武德四年……乘等五人敕住京室。于时乘从伪郑词被牵连。主上素承风问,偏所顾属,特蒙慰抚,命住胜光。[⑩]
惠乘时为隋唐间一义学名僧,备受僧俗尊崇。武德八年(625年)高祖幸国学释奠,时众推惠乘为导首讲经。正如道宣评曰:“身历三朝,政移六帝,频升中殿。面对天颜,神气箫散,映彻墙仞。自见英德,莫不推焉。”[11]能得此前辈僧的赏识,对于年轻的惠恭极为难得,故碑文用“舍利、迦叶更为显扬,文殊、普贤乐相诚仰”来类比他们之间的友谊。贞观四年(630年)十月惠乘师于胜光寺圆寂,春秋七十六。胜光寺位于京师长安西南隅,离惠恭求法所在的慈门寺很近。从行文的语气考虑,于惠乘之交往当是惠恭仍滞留于长安时的事情,这是贞观五年后惠恭方至法门寺的可靠论据。
如以上推论不谬,那么,惠恭生年可以暂定为隋大业四年(608年)至唐武德元年(618年)之间。此碑立于永昌元年(689年),时惠恭禅师仍然健在。
惠恭弘法行历大要有六:其一早年依师;其二移住法门寺;其三建三阶禅院;其四祈请舍利;其五修塔迎奉佛骨;其六刻经立碑。
据碑文,惠恭大德俗姓韦氏,“髫龄之年,已堕僧数。”髫龄,即童年,一般为五岁至十岁之间。“年甫十四,依慈门寺道场审禅师听受三□□□”。慈门寺位于长安南门之西,是“隋开皇六年刑部尚书万安公李圆通所立”[12]。开皇九年(589年)三阶教创始人信行及其弟子僧邕等因隋文帝之召请入京师传教,左仆射齐国公高颍“邀延住真寂寺,立院处之”[13]。后信行“于京师置寺五所,即化度(即真寂寺)、光明、慈门、慧日、弘善寺是也”[14]。审禅师,史籍缺载。然其属于三阶教僧人无疑。碑文中称:“心远七憎,以果收因,则含生皆佛;将时验质,则以位独凡。上根下根,洞悟其旨;真学妄学,究竟其门。”从下文分析可知,此四句实为三阶佛法核心思想的概括。惠恭依从审禅师为师,大概在武德末年。此时信行弟子本济的徒弟道训、道树仍在慈门寺传播三阶教。惠恭于慈门寺“苦行精诚,年逾十载”。然细观碑文,惠恭似乎于此十年当中又从另一禅师习禅三载。碑文称:“……禅师者,佛法之机衡,幽途之炬烛。心滋有待,智入无端。名称普闻,众所知识。”此段落颇费思量。从语气看,不象是对审禅师的赞语。因其特意标示法号,另起称呼,似指另一禅师为妥。下文复云:“稽首接足,亲承问道,摄念归依,习禅三载。”因前已讲过归依审禅师之语,故再言“归依”必指另一僧无疑。那么,这另一禅师指谁?有两种可能:一指本济弟子道训或道树;二可能指化度寺僧邕。两者相比,后者可能性更大。原因有二:其一,自从信行弟子裴玄证、本济先后圆寂后,唯有化度寺僧邕方可配得上以上赞语;其二,从惠恭所弘禅法看,与僧邕精通的僧稠一系相同(此点下文再析)。

释僧邕,俗姓郭氏,太原介休人。“年十有三,违亲入道,于邺西云门寺依止僧稠而出家焉。稠公禅慧通灵,戒行标异。即授禅法,数日便诣。稠抚邕谓诸门人曰:‘五停四念,将尽此生矣。’仍往林虑山中,栖托定门,游逸心计。”北周武帝灭法时,隐住白鹿山。隋初复兴佛教,“有魏州信行禅师,深明佛法,命世异人。以道隐之辰,习当根之业。知邕遁世幽居,遣人告曰:‘修道立行,宜以济度为先。独善其身,非所闻也!宜尽弘益之方,昭示流俗。’乃出山与行相遇,同修正节。”开皇九年,信行被召入京,僧邕随师同至京城。开皇十四年(594年)正月四日,信行圆寂。僧邕“纲总徒众,甚有住持之功”[15],实为接替信行教众的掌门人物。化度寺位于长安南门之东,慈门寺位于长安南门之西,二寺相距不远。故惠恭完全可能在不改变寺籍的情况下跟随僧邕习禅,直至贞观五年十一月僧邕圆寂为止。顺便指出,此亦可作为贞观五年后惠恭移住法门寺的考释依据之一。
惠恭移住法门寺的原因,除了法门寺本身的独特影响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法门寺所在地岐州乃是隋末唐初三阶教的流行地区之一。《续高僧传》卷三十“德美传”载,德美“开皇末岁,开化京师,受持戒检,礼忏为业。因往太白山诵《佛名经》一十二卷,每行忏时,诵而加拜。人以其总持念力,功格涅槃。太白九陇先有僧邕禅师,道行僧也。因又奉之而为师导。”[16]由此可知,隋开皇末年,僧邕曾住于距法门寺不远的太白山中弘持三阶佛法。又据唐释怀信《释门自镜录》记载,慈门寺孝慈“幼小以来,依信行禅师说三阶法,以修苦行,常乞食为业,六时礼忏,著粪扫衣。随所住处,说三阶佛法,劝诱朦俗”。“后于一时在岐州说三阶佛法。……于大斋日禅师为众说三阶法,当此之时,座下万人来。”[17]此记载本是其它宗派为丑化三阶教而写下来的。然而剔除其夸张扭曲之处,仍可见出当时三阶教对于岐州僧俗的影响。孝慈于扶风传三阶教恰为隋末唐初。这些,都为日后惠恭的弘教事业打下了基础。
惠恭移住法门寺后,“上士稽首,中庸归命”,影响逐步扩大。数年后,惠恭觉得“惠日明代,非开寂灭之域,遂别安禅院,清净住持。”至此,方才与三阶教僧不与别宗僧人杂居的规定相合。三阶禅院的建立,说明法门寺三阶教僧人已有了相当数量,信徒已较广大,且于法门寺佛事中占据相当地位。是为惠恭法门寺站稳脚跟的标志。顺便指出,有人依据“清净住持”之句将惠恭称作法门寺住持[18]是不对的。此处之“住持”二字为“轨持正法”之意,与寺院僧职不相干。
碑铭再曰:“夙夜翘诚,供养灵塔”,此是惠恭又一重大举措,也符合三阶教僧人见一塔影皆旋转礼拜的修持方法。更重要的是,可借此唤起信众对三阶佛法的信仰,故而惠恭“便烧二指,发菩提心”,请出埋于塔基下的佛骨示众。“清净大众,宛如初会。倏睹尊仪,情如新灭。岂止灵光浮景,空惊迦叶之心;实相澄辉,似入阇王之梦。”可见,此次剖示佛骨舍利,崇拜的人数也相当多,许多人都看到了舍利及舍利所射出的灵光。这就是碑文所讲的“贞观之末,沐浴舍利”之事。这次剖示,仅见于此碑记。大概距贞观五年剖示相距仅十多年,而与后来僧俗杜撰的“三十年一开”的所谓“古制”不合,故皆隐匿不载而已。
显庆元年(656年),高宗敕令法门寺僧惠恭、意方主持整修佛塔,并“施绢三千匹”,以为供养。一九八七年出土于法门寺塔下地宫中室右壁顶部的惠恭“支提之塔”残碑,仅碑铭尚存,文曰:“大唐岐州歧阳县法门寺检校佛塔大德惠恭支提之塔”。由此可证,唐高宗曾敕封惠恭为“检校佛塔大德”之号。这次重修,工程浩大,不仅将塔上用材总换以柏,编石为基,而且以佛塔为中心从整体上完善了法门寺的基本格局。据宋元载记,唐代法门寺有二十四院。有唐一代,对法门寺的整修数此次规模为最大,故而可知,即使二十四院于此时并未完全形成,仍可能至少已具备二十四院十之七、八。据唐代宗大历十三年(778年)张彧撰《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并序》载,惠恭、意方:“遵睿旨,购宏材,征宇县之工,写蓬台之妙,咨□匠而藏制,献全摹以运斤,不日不月,载营载葺。”经过此次重修的法门寺已是“危槛对植,曲房分起。栾栌沢拱,枕坤轴以盘郁,梁栋攒罗,拓乾罔而抱头。丽穹崇岳,立杖一柱以载天。蜿蜒霞舒,揭万楹而捧日。”[19]这里面无疑凝结着惠恭大德的心血和智慧。用佛家的话讲,无论对于唐代的佛教,还是对于法门寺历史文化,都是功德无量的。
其实,显庆元年开始的修葺法门寺塔寺的工程,只是数位僧人策划的鼓励高宗迎奉佛骨的第一幕。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记载:
显庆四年九月,内有山僧智琮、弘静见追于内,语及育王塔事,“年岁久远,须假弘护。”上曰:“岂非童子施土之育王耶?若近有之,则八万四千之一塔矣。”琮曰:“未详虚实。古老传云,名育王寺,言不应虚。又传云,三十年一度出。前贞观初以曾出现,大有感应。今期已满,请更出之。”上曰:“能得舍利,深是善因,可前至塔所七日行道,祈请有瑞,乃可开发。”即给钱五千、绢五十疋,以充供养。(下线为笔者所加)[20]
从引文的划线语句可以看出,唐高宗李治在智琮、弘静游说之前并不知晓法门寺佛骨之事(贞观五年李治才五岁!)。“三十年一开”既标为“传言”,无异于说其并非确凿不移之事实。说到底,可理解为数位僧人力图为以后定期迎奉佛骨所拟定的理想周期而已。其实,高宗之前,法门寺佛骨只具有地区意义,并未有全国影响。为了唤起高宗对佛骨的崇信,智琮、弘静等僧人共同导演了一出虔诚得舍利的“瑞相”,请观下文:
琮与给使王长信等十月五日从京旦发,六日逼夜方到。琮即入塔内,专精苦到。行道久之,未有光现。至十日三更,乃臂上安炭就而烧香,懔厉专注,曾无异想,忽闻塔内像下振裂之声,往观乃见瑞光流溢,霏霏上涌,塔内三像足各各放光,赤白绿色,缠绕而上,至于衡桶合成帐盖。琮大喜踊,将欲召僧,乃睹塔内畟塞,僧徒合掌而立,谓是同寺。须臾既久,光盖渐歇,冉冉而下,去地三尺,不见群僧。方知圣隐,即召来使,同睹瑞相。既至像所,余光薄地,流辉布满,赫奕润滂,百千种光,若有旋转,久方没尽。及旦看之,获舍利一枚,殊大于粒,光明鲜洁。更细寻视,又获七枚。总置盘水,一枚独转,绕余舍利,各放光明,炫耀人目。琮等以所感瑞具状上闻。敕使常侍王君德等送绢三千疋,令造朕等身阿育王像,余者修补故塔。仍以像在塔,可即开发出佛舍利,以开福慧。[21]
由僧人的游说和“灵瑞”的感化,高宗方才下定了迎奉佛骨的决心,“显庆五年春三月,下勅取舍利往东都入内供养。”[22]“皇后舍所寝衣帐直绢一千匹,为舍利造金棺银椁,数有九重,雕镂穷奇。”[23]两年后,佛骨方从东都洛阳奉迎还本塔。显庆年间的迎奉佛骨,是唐代确立法门寺为皇家寺院的关键时节,由此才真正建立了唐代“三十年一迎奉”佛骨的惯例。此前不过是“传言”而已。故深知个中原委,且亲自参与策划的道宣不由感慨系之:“三十年后非余所知!”[24]作为高宗下敕任命的“检校佛塔大德”,惠恭于此次迎奉中的作用不可低估。他曾于京师长安求法十年,熟悉朝廷的运作情况,与京城诸大德很易于同声应和。因此,这次迎奉也可以算作惠恭大德对于法门寺的又一大贡献。
至永昌元年(689年),惠恭大德于法门寺内立碑,时年七十岁左右。立碑之举费解处有二:一是碑文之叙述人称;二是立碑动机。碑铭称为“[法]门惠恭[大]德之碑”,碑尾又署“法门寺僧惠恭树”,文内又有不少颂扬溢美之辞。从碑刻署名看,应为自我立碑。这种自我颂扬的做法甚为罕见,然而信行弟子裴玄证就“生自制碑,具陈己德,死方镌勒,树于塔所。”[25]要之,惠恭此举系摹仿前辈而为。碑文虽以第三人称道之,实际上侧重于阐述惠恭的佛学见解,故又不同于裴玄证之举。问题是,惠恭为何要刻经于石碑呢?一般而言,佛经刻石原因有二:一是因纸或帛易于损坏,不便长久保存,而以石刻之则易久存;二是因北魏、北周两次灭佛,加深了佛教徒的末法思想,刻藏石经遂成风气。如“北齐慧思大师虑东土藏教有毁灭时,发愿刻藏,閟封岩壑中。座下静琬法师承法嘱咐”[26],前后继之,竟成著名于世的“房山云居寺石经”。惠恭刻经之动机已超出这两条原因,他自言为“昭其未悟”,明显面对当世。因为依三阶教看来,当世即已经是“末法”时期。这与静琬等刻石经面对将来,明显不同。尽管如此,刻经之事与信行之主张相悖,这是否意味着三阶教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呢?这需要从惠恭佛学见解上去分析。
学术界一向以为三阶教最具特色的是“无尽藏”。那么,惠恭是否在法门寺建立了“无尽藏院”呢?从现有资料难有定见。然而碑文中有“□报先于施作”,“缘道始于檀为”之句,“施作”、“檀为”均指“布施”。从显庆年间修建法门寺的工程量考察,仅仅凭朝廷的赏赐是不够的。惠恭“购宏材,征宇县之工”[27],似有动员民众之意。此外,唐高宗为何选中惠恭主持修塔事宜,其三阶教僧人的作风也有可能为高宗一种考虑的因素。征之于唐代资料,未发现朝廷赏赐法门寺土地、税赋之记录,而每次迎奉,帝王、官宦、民众均奉施大量财物。种种迹象,使我们倾向于推定法门寺院经济可能仿“无尽藏法”组织。当然,此判断还有待于进一步证实。
三、惠恭禅师之佛学思想
如上所论,惠恭实为三阶教的第二代传人,其学说基本内容是与信行大师一致的,当然也有一些变化。这种变化恰好构成了惠恭佛学思想的特色。
三阶教法乃是中国佛教史上极其特殊的一个宗派。其创始者信行在强烈的末法意识支配下,树立了独特的教义。三阶教义有两个基本的理论前提:一是“对根起行”:二是时当“恶世”。这两条构成了三阶判教的依据。唐释怀感在《释净土群疑论》卷四中说,信行“禅师立教之意,以当根佛法为宗”[28]。隋费长房亦言,其“号曰对根起行、幽隐指体(相)标榜,(然)于事少潜。”[29]这种概括抓住了三阶教的核心。信行认为,众生的根性随时而不同,因此每一个时代就须有适合该时代众生的佛法,而不能一成不变地代代相沿。化度众生时,最重要的原则是依据各时代众生之根性,而教以适当的修行法门,此即所谓“习当根之业”[30],也即因病予药。信行按照“时”“处”“人”三类将释迦成佛以来的佛教分为三个阶段,即所谓“三阶”。《三阶佛法密记》卷上言:
佛在世,佛自主持佛法,位判是第一阶时;佛灭度后一千五百年已前,由有圣人及利根正见成就凡夫住持佛法,位判当第二阶时;从佛灭度一千五百年已后,利根凡夫,戒定慧别解别行,皆悉邪尽,当第三阶时。
信行以为当世时值末法,处于秽土,人皆破戒破见,故属第三阶。第三阶佛法内唯有一切行坏、体坏、戒见具破、颠倒一切一种众生。这就是信行对当世佛法所面对的世间的判定。作为三阶教之传人,惠恭完全接受了这一结论。碑文中出现的诸如“群蒙”、“尘界虽暗”、“五浊”恶世等,其意灼然可见。碑文又曰:“正像既迁,二阶无实,□□□□”,后面四字已缺,但仍可理解为:正法、像法已经逝去,唯有末法降临。惠恭禅师为此忧心如焚,“悔叹业像奔驰,将沦教戒,爱马腾跃,先亡苦空。”此句中,“亡”通“无”,言其三阶众生愚昧而无“苦空”之见,沉溺享乐。正如《三阶佛法密记》卷上所言,“就行明时”,“就病明时”,三阶众生均为“纯邪无正位”,这就是碑文中“将时验质,则以位独凡”一句的含义。面对如此“邪恶”之世界,惠恭不禁发出了“非我法王,谁救沦溺”的叹息,亟盼“法王”释迦佛应世济度众生。
依据“对根起行”的原则,信行以为“佛所说经,务于济度。或随根性,指人示道。或逐时宜,因时判法。今去圣久远,根时久异。若以下人修行上法,法不当根,容能错倒。”[31]因此,三阶教认为,第一阶根机之众生,学三乘法,而五浊恶世的第三阶众生,则只能学“普真普正佛法”(简称“普法”)。日本道忠所著《群疑论探要记》卷六曾引《三阶集录》云:
第三阶若学普法,不堕爱憎,不谤三宝,唯有纯意,无有损坏。此“普”亦名生盲众生佛法。譬如生盲不分众色,普法亦尔。于一佛乘及三乘法,不论是非,普能信故。于诸贤圣及一切凡夫,莫辨胜劣,俱归敬。
敦煌残卷《对根起行法》中,信行论之更详,要点如下:“问曰:‘同是佛法,何因普法学之淳益无损,别法学之即损益具有?何义?’答:‘因根别故。有二义:一普法无病;二别法就根。’”因此之故,第三阶根机的末法众生,要想得到解脱,信一个佛、念一种经、学一种法,是不行的。甚至“若学一切名相别真别正佛、读经、诵经、讲律、讲论、归僧、度众生、断恶、修善、解行、求善知识、与出家人作师僧、上坐、寺主、法师、律师、论师、禅主及章疏问答人”等等,不但都不能得解脱,而且“俱名邪魔六师外道”。[32]必须“普归一切佛尽,归一切法尽,归一切僧尽”[33],必须正学一切普真普正佛法,才能“真善成就”。为了强调“普法”的意义,信行还提出了所谓“法界七普:普凡普圣、普善普恶、普邪普真、普大乘普小乘、普空普有、普世间普出世间、普浅普深。”[34]一言以蔽之,所谓“普法”之“普”,就是普遍信仰一切,甚至包括五浊恶世的三阶众生。
《惠恭大德之碑》中,关于其修行之法涉及不多,但仍可看出其遵循“普法”的痕迹。碑文中称“静乱殊学,遵行五众,虔奉四依”就是一例。关于“静乱”,《对根起行法》言:
三阶出世处所不同所由义者,于内有三段:一者,第一阶一乘根机凡夫菩萨等入道处,莫问聚落山林,静乱俱得道。何以故?由从无始以来学普行故。二者,第二阶三乘根机众生入道处者,唯在静处,不得在聚落。何以故?由从入佛法以来常学禅定根机,唯有静处能长道故。三者,明第三阶空见有见众生出世处者,唯得在聚落,不得在山林闲静。何以故?由从无始以来与如来藏佛、佛性佛、形象佛最有缘故。[35]
由此可见,三阶佛法与传统佛法修道之处有别,故曰“静乱殊学”。“四依”即《维摩诘经》所言维摩四依:“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三阶典籍中多次出现“邪四依”[36]的说法以显己义。敦煌残卷《三阶佛法》卷三中,信行驳斥教界说:“所引经等说法,俱名邪魔六师外道经法,不依法唯依人,不依义唯依语,亦名绮饰文辞,亦名庄严文饰。”在信行看来,凡不遵循“依根起行”之三阶佛法之人都是“邪四依”者,唯有他才是“四依菩萨”。事实上,“三阶禅师等,咸以信行禅师是四依菩萨。”[37]可见三阶教内正是这样崇信教主的。因此,碑文中“虔奉四依”可作两种解释:一是指“维摩四依”;二是“四依菩萨”信行。碑文中又有“四依挺出”之语,此处之“四依”仅有一义,指“维摩四依”。不管怎样理解“四依”,三阶教所谓“了义经”即指信行撰集的《三阶别位录集》、《对根起行杂录》等。所谓“虔奉四依”自然包含虔奉三阶教典籍的含义。三阶教僧人将有别于己宗的佛法称为“别法”、“妄学”,而将三阶佛法称为“普真普正佛法”、“真学”。碑文中称惠恭“上根下根,洞悟其旨;真学妄学,究竟其门”,俨然为一三阶教大师矣!惠恭至法门寺后,始终以弘扬三阶佛法为己任,故碑文云:“顿渐宗印,终始住持”。这里的“顿渐”有其特殊含义,与道生及后来的禅宗所言全不相同。《三阶佛法密记》卷上云:
问曰:何为渐而言顿说?答:法有前中后际说,有隐密显了义。隐密者为渐说,显了者为顿说。谓佛为第二、第三阶人说大乘、小乘及世间义,是隐密义说,中际法说。第三阶不尽前际说,彼无始非三乘种,毕竟不得出世说。第二阶不尽后际说,彼永入无余涅槃,身智俱灭,毕竟不成佛故。后虽为不定根者受记作佛,犹为定根二乘,不为说究竟一性常乐我净,故是名渐。为第一阶翻(反)此不顿。[38]
这即是说,第三阶佛法为“渐说”,与第一阶之“顿说”不同。日本所传《三阶佛法》卷二又有“廿四明”。其中前“五明”为“得顿灭”,后“十九明”为“得顿不灭”,似乎有统一第一阶佛法与第三阶佛法之义。可惜,文义模糊难于尽解。从碑文“顿渐宗印”看,三阶教义中“顿渐义”很关键。不过,上引诸语“渐而言顿说”其意为何,只能存疑。
依《对根起行法》所载,三阶佛法主要有三项内容:“普敬”、“认恶”与“空观”。“普敬”是先礼敬众生之本体,从而普敬一切具有如来藏的众生。“认恶”是体认第三阶众生之颠倒错谬,亦即体认一切利根空见有见众生,行坏体坏,戒见俱破。“空观”是体认所学一切解行之毕竟空寂而无所得。又据现存之《信行遗文》可知,第三阶众生具体的修行方法有四:“一、行四种不尽行,日日不断地礼佛、转经、供养众生与供养众僧。二、随喜助施。三、依十二头陀,常行乞食。四、依《法华经》行不轻行。”[39]修行上述四大类法门时,必需日日不断,精进以赴,即不断地诵经、布施、苦行等等,直到成佛为止。上述法门的实质在于,不论一乘三乘之是非,不承认一切圣贤凡夫之胜劣的区别,普遍归于大小乘,普遍归敬一切根机之众生。这种“普敬”之法来源于《维摩诘经·香积佛品》:
菩萨成就八法,于此世界,行无疮疣,生于净土。何等为八?饶益众生而不望报,代一切众生受诸苦恼,所作功德尽以施之,等心众生,谦下无碍,于诸菩萨视之如佛,所未闻经闻之不疑,不与声闻而相违背,不嫉彼供,不高己利,而于其中调伏其心,常省己过,不讼彼短,恒以一心求诸功德。是为八法。
信行为此“八法”找到了佛性论依据,遂将其改造为:
一切八种佛法:一者如来藏佛性;二者普真普正佛法;三者无名相佛法;四者以圣法中拔断一切;五者悉断一切诸语言道佛法;六者一人一行佛法;七者无人无行佛法;八者五种不忏尽佛法。[40]
此“八法”含义颇杂,兹不全解。其中“一人一行佛法”,“一人者,自身唯是恶人,一行者如《法华经》说常不轻菩萨唯行一行。”[41]明知其为“恶”众生,信徒仍须敬拜。何以故?三阶佛法认为,一切法是从唯一的如来藏展开的,所有的人都具备佛性,故一切人都无有差别,应该将一切人都当作如来藏佛、佛性佛、当来佛而敬拜。这种“普佛”思想必然成为对一切人不分爱憎轻重的普敬思想,而其理论根基是“当果”佛性论,但却是对其加以曲解而套用的。作为信行的再传弟子,惠恭禅师自然不会这么认为,他是自觉地将其写进了碑文之中。碑文称“以果收因,则含生皆佛”。唐李贞撰写的《隋大善知识信行禅师兴教之碑并序》载:“用因收果,则从因以表真;以果摄因,乃缘果而除妄。”[42]敦煌残卷《普法四佛》中又曰:
所谓正因佛性,言一切法界众生通凡及圣皆有此性,一切诸佛菩萨亦同有此性。从极果立名,故名佛性。然此佛性非因非果,在因名因,在果名果。……佛性义者,与法界常果收法界常因,故名佛性。从佛果向因,总收尽,故名佛性。[43]
从众生皆可成佛的果位观之,众生本具成佛之因性,故从“极果立名”、“以果收因”而言,含生皆具佛性,皆是佛。既然众生均具此佛性,那么其善恶、根机多么不同,一律平等,了无差别,故修三阶佛法之人必当普敬一切众生。众生“当现虽无具恒沙功德,当来具足恒沙功德,与真无别”[44],故敬“人”就是敬佛、敬如来藏。三阶教经过这种一种看似合理的思辨,为其普敬法找到了理论支点。其实,成佛的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性,作为本来的如来藏并不等同于具有如来藏的“个体”。这种“有意”的混淆扭曲,导致了其宗教实践的背谬。这也是三阶教之所以被目之为异端的原因之一。
惠恭于碑文中亦阐述了其心性论思想。“心”、“识”、“智”等名相屡屡提及。此中的“心”有二义:一是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二是阿赖耶识。敦煌残卷《普法四佛》中言:“如来藏体性真实,于一切名相作而不作,故亦名阿赖耶识。”此“真实”之如来藏为诸法相之本体。换言之,“法界名相依如来藏住,如一切波依于水故,由有如来藏故,有法界名相。”[45]“心”与“法相”是非一非异的关系,碑文称之为“心相不二”。《普法四佛》对此解释为:
法界名相即是如来藏体,相外无别体故,如一切波即是其水,波外无水故。但法界名相由一切善恶业生,不由如来藏起。如来藏功能作用周遍法界,与一切名相作依持建立本。然如来藏异于一切名相,唯藏是体,名相非体故。[46]
碑文又称“十方诸佛,从法立名;相有始终,心无坏成”。按,三阶教典籍认定佛有两种:“一者义当真佛,以真摄应,佛义具足尽……二者义当应佛,以应摄真。”[47]三阶佛法以如来藏佛、佛性佛、当来佛、佛想佛为“真佛”,称其为“普法四佛”,而以十方诸佛或“五十三佛”(见敦煌《七阶佛名经》)为“应佛”。而“应佛”是以法立名的,故其有“终始”。唯有如来藏自性清净心无有“坏成”,如信行所言:
心性不动,亦无所依,复无处所。无形无相,名解脱相;圆满不动,空如如相。若觉心空,名空入门,更无思想门,心性起无作门。知心无碍,本非系缚,名解脱门;心寂灭,名涅槃门;心无变异,名真如门。[48]
总之,“此一心法,随义立名,无住无本。”“心”是纯净无染、圆满不动的本体,故“一切无心名为圣道”,只是由于生于“无心法起分别是名烦恼”。[49]因此,世间万物也正是由此而被认定为“实有”、“一合”。“怨形妄心,显见灵塔”。此“塔”之起,全是妄心使之然,这就是碑文中“世间实有,名为一合”,“怨形妄心,显见灵塔”的含义。三阶教所言“恶法”是指“十二颠倒”。此十二颠倒“略说其是唯心,谓内心体迷,取著颠倒。”[50]要对治十二颠倒,须修“普真普正佛法”方可离“倒”为正,最终成佛。此“普法”即前述之“八种佛法”。《三阶佛法密记》卷上言:“第三阶人常纯颠倒,根中病重”之“具体相”决定其须修普法才可转“倒”为正。此“十二颠倒”及“八种佛法”“就体不异,就义名别”,故“知十二即一颠倒,如八种佛法即一佛法”。“一切八种佛法俱是普真普正故,所以八种佛法名数虽少,能多对治十二颠倒。”[51]正如惠恭碑文所言:“智越断常,心超间塔,种觉□映,一多相纳”。启“智”而修八种佛法(此为“一”)可对治十二颠倒(“多”)。这样“一多相纳”即可转“倒”为正,转凡入圣。
应特别指出,三阶教义对“识”、“智”有较独特的说法。尽管有时其典籍亦将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等同于阿赖耶识,但其亦言“就理心二本说,藏即理,世识即心也。藏为真也,识为俗也。”并言及“藏识海常住,境界风所动。种种诸识浪,腾跃而转生”。[52]惠恭碑文中言:“识海波□,□□扇激”大概就是此义。这里似乎有将阿赖耶识与六识混合的倾向。然而,《对根起行法》中又有“性八识”、“智八识”的说法:
性八识者,本识幡真成妄,对缘作六、七……本识者,即如来藏佛性是;对缘识者,于内有二种:一者对缘随染识,二者自心缘不觉识。
此处之“对缘随染识”指六识,“自心缘不觉识”指第七识。与“性八识”相应:
智八识者,本识复妄成真,名之为智。于内有二种:一者治惑智;二者对缘不染智。治惑智者起惑□,幡愚成智。对缘不染智者,有二种:一者对缘不染智,二者废缘谈体智。
此“智”中,与六识对应之眼、耳、鼻、舌、身、意皆为“对缘不染”之“六智识”。“废缘谈体智”名为第七智,即“睡眠不觉,由有智在”。[53]在此,三阶教认为,阿赖耶识具有“妄性”,可“幡真成妄”,具“生起”功能,如碑文所称“虽含觉性,不废愚蒙”。而“智八识”则是纯净无妄的,可“幡愚成智”,即使通常被说成为“妄”的六识,也可由“性六识”转为“六智识”。从一些材料可以看出,三阶教似乎将“识”看成一体两面,故其转识成智乃于同一本体上完成。当然,三阶教义并不完善,也并不太严密。如上所引,先言“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亦名阿赖耶识”,又言“理心二本”,似乎如来藏与“心”是两个本体。时而认为“心”如如不动,时而又认为“心”为俗。这些混乱之处历历可见。这可能与流传下来的典籍并非其精华有关。至于惠恭所处唐初之三阶教义是否克服了这种混乱,资料匮乏,难于尽言。故于此只能引早于惠恭的材料考释,失惠恭原旨之处可能在所难免。
除了“普法”之外,如同隋唐之际北方大多数僧人一样,三阶教僧人亦修习禅法。信行、本济、僧邕等均被道宣列入《续高僧传·习禅部》。然而,从现存资料看,信行并不太重视禅法。尽管其典籍中屡次提及禅定,但仍嫌散乱而缺乏系统。从信行行历看,他并未系统地修习禅法。其师祖慧瓒“大小经律,互谈文义;宗重行科,以戒为主;心用所指,法依为基”[54],并非专精禅法。信行为沙弥时尝从慧瓒学,后归瓒之弟子明胤禅师。慧瓒、明胤二僧“其所开悟,以离著为先。身则依附头陀,行兰若法。心则思寻念慧,识妄知诠。”[55]只是将禅法作为静心离念的辅助手段,主要是苦行(即“头陀行”)为主。受其师影响,加之信行体质不佳,不堪久久坐禅,故信行对禅法并不看重。三阶僧人虽号称禅师,然大多未有明确、严格的禅法传授系统。信行弟子中唯有僧邕情况特别。僧邕十三岁就依止僧稠禅师出家。僧稠曾归依少林寺佛陀禅师,以专弘“四念处法”及“十六特胜法”闻名于世,此禅系为隋唐之际两大禅系之一。在开皇初年归依信行门下之前,僧邕修习禅法二十余年,深达其堂奥,僧稠对其赞赏有加。碑文言,惠恭于长安“习禅三载”,又屡次提及禅法,如“明性起于禅枝”;“定镜流辉,尘清四念。心珠凝彩,照引三明”;“定水澄影,迷津息问”。如此等等,显然,重视禅法,继之有统,乃是惠恭修行的特色之一。从碑文可知,惠恭仍以“四念处法”为其禅悟门径,很可能为僧稠--僧邕一系禅法的传人之一。
信行明确反对读经、诵经、讲经,当然这里的“经”指别派之“经”,不包括三阶典籍在内。对于佛经、义理的轻视、疏远是三阶教最大胆、最具反传统色彩的主张。敦煌残卷《三阶教法》卷三曰:“若学一切名相、别真别正佛、读经、诵经、讲律”等等,“俱名邪魔外道。”三阶教典籍是信行抄录共约四十种经文编写而成的。当有人问何故抄出三阶佛法时,信行言:
同故得抄出,异故须抄出。异有三义:一者所为人不同;二者所说法不同;三者为人说法广略、兼正不同。佛为第一阶、第二阶上根人说出世义,微细浅近,真身、应身,一乘、三乘,大乘、小乘,普别具说。为第三阶位上邪见成就不可转人说世间义,兼为第一阶、第二阶下根人同说普真普正佛法。又广略不同。佛广说第一阶、第二阶,略说第三阶。今广说第三阶,略说第一阶、第二阶。故须别为第三阶人抄略广说普真普正佛法。[56]
信行认为,佛所说“经”、“法”主要针对第一阶、第二阶众生,虽也有针对第三阶众生而讲的,但只涉及“世间义”,未说“真实法出世义”。因此,有必要将佛经中专为第三阶众生而讲的经论摘编出来,加以新的阐释,号称“别为第三阶人抄略广说”。尽管信行未敢明言,实质上他是想用《三阶佛法》代替佛经,故自己可以抄经,而不许别人抄经、诵经。日本所传《三阶教法》卷四有云:“于佛经内,抄前抄后,抄后著前,前后著中,中著前后,当知如是诸恶比丘魔伴侣。”就连载有三阶教信奉的“常不轻菩萨”的《法华经》,三阶教亦一概反对读诵。有僧孝慈“劝彼持《法华经》优婆夷等言:‘汝等持《法华经》,不当根机,合入地狱。’”[57]这样对照一下,惠恭于法门寺刻写《佛遗教经》、《般若心经》,且明曰“昭其未悟”,明显有“借教悟宗”的倾向,显然与其祖师所倡不一致。这可以看作惠恭大德“离宗背道”的一个方面。
惠恭立碑刻经并不是偶然行为。碑文有云:“道存□□,□执油于副墨”;“理归微渐,见法雨于临墀”;“寂静律仪,则睹文齐相;澄清等忍,则观义忘言”。此可看作其刻经的理论宣言。其中,最后一句论“相”与“文”、“言”与“义”的关系,认为可以借助文字观相,也可凭借言悟义,不过最终须得意忘言而已。第一句中,“副墨”指文字,源于《庄子·大宗师》:“南伯子葵曰:‘子独恶乎闻之?’曰:‘闻诸副墨之子。’”第二句中,“墀”意为高台,在此指讲台、讲堂。这样看来,惠恭的意思很明确,尽管其道隐微难言,但完全可通过文字得其真意,亦可于讲经、诵经中得其旨归。正因为如此,惠恭于碑文中写道:“碑若天工,字凝神运,密严显迹,含性招训。”不过,惠恭为何专刻《佛遗教经》和《般若心经》呢?可能有三条原因:一是这两部经都很短小,便于纳于一石;二是《遗教经》讲“以戒为师”,《般若心经》讲“般若空观”,“戒”与“空观”均是三阶教义所重;三是,这两部经都是唐初教界及朝廷所重。唐太宗于贞观年间曾专门下诏颁布《《〈佛遗教经〉施行敕》:
令所司,差书手十人,多写经本,务在施行。所须纸、笔、墨等,有司准给。其官宦五品已上及诸州刺史各付一卷。若见僧尼行业与经文不同,宜令公私劝勉,必使遵行。[58]
因此缘故,《佛遗教经》十分普及。《般若心经》为玄奘于贞观二十三年译出。未几,弘福寺沙门怀仁历时二十五年集得王羲之字迹制成《般若心经》碑石。有唐一代,《遗教经》及《般若心经》不断被书写刻石。从这个角度看,惠恭选中这两部经刻石,也有迎合朝廷、僧俗的动机。
作为三阶教僧,惠恭无疑是其教义的忠诚信仰者和坚定实践者。然而,惠恭重视禅法,看重讲经、诵经,明显与信行的传教风格不同。这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随着时代的变化,三阶教的“异端”色彩受到了许多僧人的批评,其生存面临着许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三阶僧人也有所分化,在一些僧人身上表现出了向传统佛教回归的倾向。惠恭大德就是这样一位僧人。证之于武周圣历二年(699年)敕文:“其有学三阶者,唯得乞食、长斋、绝谷、持戒、坐禅。此外辄行,皆是违法。”[59]可见,如惠恭所为,在唐初三阶教内当较为普遍。当然,也有固守信行立场的人,如前述之孝慈及武周时期的净域寺的法藏。释法藏,俗姓诸葛,苏州吴县人。年十二岁出家,伏膺净域寺钦禅师。法藏对于信行之教旨“守而勿失,作礼奉行”,以为“镕金为像,非本也;裂素抄经,是末也。欲使贱末贵本,背伪归真,求诸如来,取诸佛性。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众生对面而不识,奈何修假以望真?”[60]法藏于开元二年(714年)十二月十九日圆寂,春秋七十八。这位法藏稍晚于惠恭,于当时亦有较大影响,代表了唐初三阶教的正统作风。
总之,惠恭于唐初三阶教贡献较大。他看中了处于上升时期的法门寺,于其中建立了三阶禅院,并得到了朝廷的首肯以及民众的信仰,高宗敕封其为“检校佛塔大德”。按,此处之“检校”,当为僧职名称。“检校”本为朝廷散官名称,东晋时有检校御史,唐有检校官,如检校司空、检校礼部尚书等。[61]还有,净域寺法藏亦得武后崇信,“如意元年,大圣天后闻禅师戒行精最,奉制请于东都大福先寺检校无尽藏。长安年又奉制请检校化度寺无尽藏。其年又奉制请为荐福寺大德。”[62]有学者[63]误以为“检校”为“检抄”之意,似乎武后曾下令大规模地清理三阶教寺院的“无尽藏”。从惠恭于法门寺的行历,我们有理由认为,唐初朝廷并未特别的压制三阶教,基本上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不仅如此,朝廷还对著名的三阶教僧人有所奖掖,如僧邕圆寂后“主上(太宗)崇敬情深,赠丝帛为其追福”,“左庶子李百药制文,率更令欧阳询书文。”[64]又,唐书述《两京新记》载,化度寺无尽藏院“贞观之后,钱帛金绣,积聚不可胜计,常使名僧监藏”。不过,唐初朝廷未加限制,但也未曾如对其它教派一样扶持其发展。三阶教义是对两次灭法的直接反应。这种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反映了社会动乱、佛法遭劫的情形。一旦政治形势稳定,“国泰民安”,这种描述对统治者来说,无疑是一种诽谤、诬蔑,因此,引不起统治者的好感。另一方面,信行以普法标榜宗门,将其它派别一律视为“别派”,特别是对佛经的疏远,引起佛教内部普遍的反对。唐代许多史籍中均载有三阶教僧人遭恶报的传闻。随着各宗派的形成、壮大,压制三阶教成为各宗题中应有之义。从这个角度言,与其将三阶教的衰落甚至消亡的主因归之于朝廷的禁断,毋宁归之于佛教内部的反对浪潮。而这一浪潮的兴起,其根本原因在于三阶教义已经不太适应当时现实的需要。正是教内的强烈反对推动了朝廷对三阶教态度的转变。武后的禁断令,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其它派别僧人的鼓动,而非出自武则天之本意,故其未能行之深广。即就是颇为严厉的“开元年禁断令”,也未能阻止三阶教的继续流传。德宗甚至允许将三阶典籍编入《贞元录》。[65]之所以如此,乃是因朝廷并未生坚决禁断之心,故其态度一直摇摆不定。甚至遭到“会昌灭佛”的打击,三阶教方告消亡。总括三阶教的传播历史,基本上是自生自灭而已。
(原刊发于《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1期。)
--------------------------------------------------------------------------------
[①]分别见于陈景富著《法门寺史略》,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韩金科、王均显撰《新发现唐法门寺住持〈惠恭禅师大德之碑〉》,《文博》(西安),1991年第4期;李发良著《法门寺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②] 此行未满。
[③] 此行未满。
[④] 此行未满。
[⑤] 此行未满。
[⑥] 此行55字,“生”字乃添加小字。
[⑦] 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大正藏》第52卷,第406页中。
[⑧] 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大正藏》第52卷,第406页下。
[⑨] 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大正藏》第52卷,第406页下。
[⑩]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25,《大正藏》第50卷,第633中-634页上。
[11]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25,《大正藏》第50卷,第634页下。
[12] 宋宋敏求《长安志》卷10,《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第125页,中华书局版。
[13]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16,《大正藏》第50卷,第560页上。
[14]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16,《大正藏》第50卷,第560页上。
[15] 此段引文均见唐道宣《续高僧传》卷19,《大正藏》第50卷,第583页下-584页上。
[16]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29,《大正藏》第50卷,第697页上。
[17] 唐释怀信《释门自镜录》卷上,《大正藏》第51卷,第806页中。
[18] 参见韩金科、王均显《新发现唐法门寺主持<惠恭禅师大德>》,《文博》1991年第4期。
[19] 唐张彧撰《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并序》,《全唐文》卷516。
[20] 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大正藏》第52卷,第406页下-第407页上。
[21] 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大正藏》第52卷,第407页上-中。
[22] 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大正藏》第52卷,第407页中。
[23] 唐张彧撰《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并序》,《全唐文》卷516。
[24] 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大正藏》第52卷,第407页中。
[25]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16,《大正藏》第50卷,第560页中。
[26] 明刘侗《帝京景物略》。
[27] 唐张彧撰《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并序》,《全唐文》卷516。
[28] 唐怀感《释净土群疑论》卷4,《大藏经》第47卷,第50页中。
[29]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12,《大正藏》第49卷,第105页下。括号内文字为笔者所加。
[30] 唐李百药《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全唐文》卷143。
[31] 唐唐临《冥报记》卷上,《大正藏》第51册,第788页中。
[32] 敦煌《三阶佛法》卷3,第4页,见《大藏经补编》第26册,第270页,华宇出版社版。
[33] 敦煌《对根起行法》第4页,《大藏经补编》第26册,第329页。
[34] (日)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第475页。
[35] 敦煌《对根起行法》第17页,《大藏经补编》第26册,第343页。
[36] 如《三阶佛法密记》卷上曰:“四者谓邪四依:一依人不依法;二依语不依义;三依识不依智;四依不了义经不依了义经。”见《大正藏补编》第26册,第303页。
[37] 唐怀感《释净土群疑论》卷3,《大正藏》第47卷,第48页上。
[38] 敦煌《三阶佛法密记》卷上,第36页,《大正藏补编》第26册,第324页。
[39] 此据蓝吉富先生的概括,见其主编的《大藏经补编》第26册第211页附录。
[40] 敦煌残本《三阶佛法》卷3,第9页,《大正藏补编》第26册,第274页。
[41] 敦煌《对根起行法》第25页,《大藏经补编》第26册,第351页。
[42] 李贞为唐太宗之子,封越王。武后称制,越王起兵反之,兵败自杀。时为垂拱四年(688年)。故此碑当撰于惠恭立碑之前。文见《唐文拾遗》卷12。
[43] 敦煌残本《普法四佛》第5页,《大正藏补编》第26册,第423页。
[44] 敦煌《对根起行法》第31页,《大藏经补编》第26册,第357页。
[45] 敦煌残本《普法四佛》第1页,《大正藏补编》第26册,第419页。
[46] 敦煌残本《普法四佛》第1-2页,《大正藏补编》第26册,第419-420页。
[47] 敦煌残本《三阶佛法》卷3,第3页,《大正藏补编》第26册,第269页。
[48] 《信行□集真如实观起序》卷1,第5页,《大藏经补编》第26册,第410页。
[49] 此处引文均见《信行□集真如实观起序》卷1,第5页,《大藏经补编》第26册,第410页。
[50] 敦煌《三阶佛法密记》卷上,第14页,《大正藏补编》第26册,第302页。
[51] 敦煌《三阶佛法密记》卷上,第17页,《大正藏补编》第26册,第305页。
[52] 敦煌残本《普法四佛》第2页,《大正藏补编》第26册,第420页。
[53] 此处引文均见敦煌《对根起行法》第29页,《大藏经补编》第26册,第355页。
[54]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18,《大正藏》第50卷,第575页上。
[55]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18,《大正藏》第50卷,第575页上-中。
[56] 敦煌《三阶佛法密记》卷上,第11-12页,《大正藏补编》第26册,第297-298页。
[57] 唐怀信《释门自镜录》卷上,《大正藏》第51卷,第806页中。
[58] 《全唐文》卷9。
[59] 唐明佺《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卷15,《大正藏》第55卷,第475页上。
[60] 唐田休光《法藏禅师塔铭并序》,《全唐文》卷328。
[61] 参见《文献考通》卷64“职官类”。
[62] 唐田休光《法藏禅师塔铭并序》,《全唐文》卷328。
[63] 参见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198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64]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19,《大正藏》第50卷,第584页上。
[65] 日本龙谷大学藏《贞元录》卷13,《大藏经补编》第26册,第445-4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