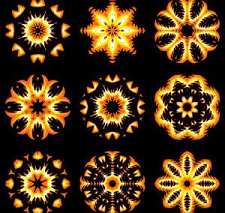关于达摩和慧可的生平
发布时间:2020-04-04 16:13:23作者:佛心网
一
关于达摩的最早传记史料是《续高僧传》的“达摩传”[1]。据该传说,达摩是南天竺人,婆罗门出身,因悲愍此边隅之国,欲以正法相导,故而远度汉土。初抵中国,是在刘宋时代(424—479),所到达的地方是“南越”,就是海南岛对岸一带地方[2]。
关于达摩在南方的经历,《续高僧传》的本传中没有记载,只在“法冲传”中简单提到达摩曾将四卷《楞伽》“传之南北”、“后传中原”。据此则达摩在北渡之前有可能曾在南方传授过四卷《楞伽》。《楞伽师资记》说达摩上承求那跋陀罗,暗示达摩曾与求那跋陀罗相见。若两人真的曾经相见,则达摩至宋,当在求那跋陀罗入寂的宋明帝泰始四年(468)以前。若然,则达摩北渡之前,至少应有十余年间待在江南。则“法冲传”所暗示的在南方依《楞伽经》传禅之事,就完全有可能成立了。但是,从诸传及各种史料对此均无记载来看,达摩在南方实际上并没有留下什么足迹。
达摩是在什么时候离开南朝、北至魏土的[3],包括《续高僧传》的本传在内的早期传记,均无明确记载。但在《宝林传》、《祖堂集》这些比起《续高僧传》等来说成立时期较晚的早期禅宗史料之中,却说达摩是在北魏太和十年(486)北渡至魏的。此说虽一向未被重视,但其是否可信,则可通过《续高僧传》的“僧副传”来帮助澄清。
据“僧副传”说,僧副——一般认为他就是《景德传灯录》等中所说的达摩的弟子道副——因性爱定静,四方寻师,遂访得达摩于岩穴之中[4]。因达摩“言问深博”,遂感而从其出家。初从达摩修学禅法,“寻端极绪”,有大成就,乃至受到习定者们的尊重,所谓“为定学宗焉”者是也。后则离师,“周历讲座,备尝经论”,又于齐建武年间(494—497)南游杨辇(杨都,即金陵),止于钟山定林下寺。梁武帝仰其清风,迎至开善寺。后随西昌侯萧渊藻入蜀,而使蜀地禅法大行[5]。后又返回金陵,于梁普通五年(524)寂于开善寺,春秋六十一。
据此可推知,道副生于464年,南游时约三十余岁。若将其跟随达摩修学的时间暂且按五年来计算[6],“周历讲座,备尝经论”的时间暂且按三至五年来计算的话[7],则其从达摩出家当是在大约二十一、二岁前后(484—486)。若据此而推,则达摩至少应该在486年时,就已经到达魏地了。《宝林传》、《祖堂集》所说的达摩北渡的时间,与推算出的僧副出家时间基本一致,说明这一时间还是有相当的根据的,可以认为大体上应该是可信的。然而《宝林传》、《祖堂集》等灯录又说达摩于梁武帝普通八年(527)始达于南海,这是时间上的倒置,显然是后世的误会或附会。达摩北渡的时间实际上绝不应该是在梁武帝的时候,而应当是在齐武帝(483—493)的时候。
关于达摩在魏地的情况,《续高僧传》的本传说,达摩每止住于一个地方,就在那里传授“禅教”。但当时魏国境内“盛弘讲授”,所以乍闻达摩所传的禅法,“多生讥谤”。言外之义,讥谤是来自讲授之徒[8]。但是,却有道育、慧可两个沙门,年纪虽少,却志向高远,愿为弟子,四、五年中,承事供养,咨问习学。达摩感此二人之精诚,遂诲以真法,即所谓安心法——壁观,发行法——四法,顺物法——护讥嫌,方便法——不着。其中以理(壁观)行(四法)二入最为重要。本传谓达摩以此等法“开化魏土,识真之士,从奉归悟”,并有弟子录其言语,流传于世。这卷“言语”应当就是指《楞伽师资记》的“达摩传”所说的昙林所录的《达摩论》一卷。据该记说,《达摩论》中,除了“二入四行论”外,似乎还有别的内容,皆昙林所录。道宣“达摩传”的主要内容,应当就是根据此《达摩论》。
二
关于达摩的年纪,《续高僧传》说达摩“自言一百五十余岁”。一般皆认为这是承《洛阳伽蓝记》卷一之说,所以又都认为《伽蓝记》之菩提达摩,就是禅祖菩提达摩。但这个看法,实际上应该是一种误会。
因为第一,《续高僧传》的达摩是南天竺人,又传授流行于南天竺的《楞伽经》,其人其事,正相吻合。而《伽蓝记》的达摩则是西域波斯国的胡人,这个波斯国,因《伽蓝记》卷五有所述及,大致可知其位置在葱岭(帕米尔高原)之北的今新疆南部的地方,所以《伽蓝记》的达摩可以说是个名副其实的西域胡人[9]。第二,《续高僧传》的达摩生于中国(佛教称有佛法处为“中国”,南天竺佛法兴盛,故于佛教中可称为中国),“悲此边隅”,欲“以法相导”(《续高僧传》“达摩传”语);又“言问深博”(“道副传”语),“审其□慕则遣荡之志存焉,观其立言则罪福之宗两舍”,“摩法虚宗,玄旨幽赜”,“幽赜则理性难通”(《续高僧传》“习禅论”之语)。而《伽蓝记》的达摩则是“起自荒裔,来游中土”,显然是出身于无佛法或佛法不盛的国土;见永宁寺“金盘耀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遂“歌咏赞叹:实是神功”,恰似刘姥姥入大观园;又“自云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甚至说“极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无,合掌连日”。永宁寺即使是壮丽无比、巧夺天工,可为阎浮之冠,也不过是个世间有为之法。一位“悲此边隅”,欲“以法相导”,而又“言问深博”、“罪福两舍”、“玄旨幽赜”的智者,岂会自认是“起自荒裔”,视此“边隅”之土为中土,又如此赞叹倾倒于这样一个边隅之土所建的世间无常有为之法?第三,禅祖达摩在魏地大概只待到太和十九年(495),与《伽蓝记》的达摩在魏地活动的时期全不相合(详见下文)。所以,根据如上三点,应该断定这两个菩提达摩完全是同名的两个人。
三
关于达摩的所终,“达摩传”说是“不测”,而“慧可传”则说是“灭化洛滨”。迄今为止的研究皆认为,“慧可传”作于“达摩传”之后,应以“慧可传”所说的“灭化洛滨”为准,并根据《洛阳伽蓝记》所说,推测达摩应当灭于530年左右[10]。但是,这个看法显然过于简单了。
首先,以《伽蓝记》的达摩为禅祖达摩,据其在魏地的时期来推测禅祖达摩入灭的时间就已经不妥,上文已详。其次,达摩是慧可之师,关系确凿,达摩的传记置于慧可的传记之前,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不应该单单因为“达摩传”在“慧可传”之前,就认定“达摩传”先成,“慧可传”后成。所以,也就不应该因此而定执达摩的所终,究竟是“灭度”还是“不测”。况且,道宣作僧传,往往也不可能完全地精益求精。这一点,从达摩师徒三人传记之有失衔接,亦可窥见一斑。如:第一,达摩既然是僧副之师,则其传记理应置于“僧副传”之前,而却置于“僧副传”之后。第二,“僧副传”中虽言及达摩,而“达摩传”中却未言及僧副[11]。第三,“达摩传”中说达摩“不测于终”,而“慧可传”中却说达摩“灭化洛滨”,相互矛盾。第四,“慧可传”中已经明示,达摩至少应在东魏天平初年(534)以前就已经“灭化”,其年代应当是“魏”而不是“齐”,但目录中却称其为“齐邺下南天竺僧”。第五,取《洛阳伽蓝记》“一百五十岁”之说入“达摩传”,更进一步说明他对禅祖达摩活动的时期不甚了了(详见下文)。由此诸点来看,对于达摩的所终,绝不能依道宣所说,轻下结论。
不过,由于在同一“习禅篇”中,关于达摩的所终,出现了两种说法,遂为后世的传说提供了材料。后世盛传达摩示灭以后被埋葬在熊耳山(不是被荼毗,若被火葬就无法复生了),但后来宋云从西域回来时,又在葱岭见到了达摩携只履西归,这显然是用一种神话传说的形式将“灭化”和“不测”这两种说法杂糅在一起了——是两种说法的折中。
四
关于达摩的所终,与究竟是“灭度”还是“不测”同样重要的问题,是“灭度”或“不测”的时期。迄今为止的研究皆主张达摩灭于530年前后,而这个时间,是根据《洛阳伽蓝记》关于“菩提达摩”的记载推导而来的。但是,既然我们现在已经不能承认《伽蓝记》的菩提达摩是禅祖达摩,那么,“530年”这个时间自然也就不能认为它成立了。那么,达摩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测”或“灭度”的呢?这个问题,因为与慧可有密切关系,所以还须从慧可说起。
据《续高僧传》的“慧可传”,慧可俗姓姬氏,虎牢人,通晓内外经典,四十岁时得遇达摩,遂为弟子。达摩曾授其四卷《楞伽经》,告之曰,若能依此经修行,自得度世。达摩“灭化洛滨”之后,慧可亦“埋形河涘”,直到天平之初(534),才开始在新邺公开传禅。但不久之后又受到道恒禅师的迫害,几乎死去。之后多年流离于邺卫,曾与向居士有书信问答,并有语录行世,但始终没有对当世很有影响的弟子。周武灭法时(574)尚且在世,与同学昙林共护经像。
《续高僧传》说慧可四十岁时得遇达摩?《历代法宝记》以下,亦均谓慧可遇达摩时是四十岁。按理说,既然包括《续高僧传》在内的诸传皆认为慧可与达摩相遇时是四十岁,那么,对此说本来就不应该再有什么可怀疑的了。迄今为止也确实无人对此说表示过怀疑。但是,《楞伽师资记》的“慧可传”中却说慧可与达摩相遇时是十四岁。只是由于这是唯一一个独家异说,所以迄今为止便完全没有被研究者们所注意。但是,我们现在却应该注意到,《续高僧传》谓道育、慧可“年虽在后”,昙林的《二入四行论序》也谓道育、慧可“年虽后生”,显然都是在强调二人遇达摩时年纪尚且很轻。所以,十四岁之说亦应有其一理,不可完全无视。但是,一旦允许十四岁之说亦有一理,则自然产生了两说究竟孰是孰非的问题。
按,《续高僧传》说,达摩“灭化”之后,慧可也“埋形河涘”,直到天平之初(534)才开始公开传禅,但“埋形河涘”的时间究竟有多久,则未交代。然而《历代法宝记》却明确地说,慧可在得法之后,“四十年隐[山+皃]山洛相二州”,据此说,则慧可与达摩分手后,先后在[山+皃]山[12]及洛相两州埋形隐迹达四十年之久,然后才出世说法传禅。不过,由于此乃《历代法宝记》的独家之说,所以历来并未受到重视。但若以埋形隐居按四十年来计算,出世传禅的时期按《续高僧传》所说的“天平之初”(534)来计算的话,则慧可与达摩分手的时间,应当是在大约北魏太和十八年(494)的时候。而这个时间正好与《宝林传》、《祖堂集》和《景德传灯录》所一致主张的达摩于太和十九年(495)示灭的时间相吻合[13]。而且这一时间与《宝林传》、《祖堂集》所说的达摩在北魏太和十年(486)北渡至魏的时间正好相距九年,因此与古来达摩在嵩山面壁九年的传说也正好相吻合。
并且值得注意的是,达摩的另一个弟子僧副,也是于495年前后(齐建武年间,494—497)离开魏地南下金陵的,与如上三说的时间亦正好吻合。如果将这些线索结合起来看的话,这一时间上的一致,显然不是巧合,而应当认为这都是与达摩在太和十九年(495)时确实已经不在魏地有关——师不在魏地了,弟子们也就都远走他方了[14]。
为什么达摩不在魏地的同时,弟子们也都远走他方了呢?要想明白个中的原由,我们应当注意一个所有达摩和慧可的传记都记载了的重要事实,那就是,自达摩在魏地传禅开始,他这一派的禅法,就一直受到讥谤。
关于达摩受到讥谤的原因,《续高僧传》说是因为当时魏地“盛弘讲授”,所以“乍闻定法”,便生讥谤。这意味着讥谤是来自于“讲授”之徒,是义学对定法的讥谤。然而,昙林所记则没有这个限定,而是泛指讥谤达摩一派的是“取相存见之流”。这两种说法究竟哪一个正确呢?
按,根据各种记载,当时魏地并不是没有“定法”,而且其“定法”还由来已久。早在太武帝时(424—451),即有禅僧玄高于平城弘扬禅法,为北魏僧人最早之领袖。文成帝(452—465)时,有沙门统昙曜为复兴佛法之栋梁,亦以禅法着称。同时又有僧周亦以头陀坐禅闻名于世。及至献文帝(465—471)禅位于太子(孝文帝),移居于北苑崇光宫,览习禅籍,又建鹿野佛图于苑中之西山,备有岩房禅堂,禅僧居其中,可见其自身与禅僧之交往,及对禅法之热衷。孝文帝世(471—499),虽特崇义学,成实、涅槃、毗昙均因之以大兴,而亦有禅僧佛陀为孝文帝所敬,在平城时为其另设禅林,南迁后于洛都设静院以居之,后又于嵩岳少室山为之立寺(即少林寺),公给衣食。这些事情,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第十四、十九章,所述甚详。故知魏地非无定法,亦非不重定法,所以不能单纯地认为达摩的定法受到讥谤,是因为魏地盛弘讲授的缘故。
《续高僧传》所说既然与实情不符,那么,昙林所说的又如何呢?
汤用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论及北朝佛教时,反复强调的是,北魏朝廷上下之奉佛,首在建功德、求福田饶益,所以造塔立寺,穷土木之功,乃是北朝佛教的最大特征。塚本善隆的研究(《北朝佛教史研究》)也可以说明这一点。而这一点,正意味着北朝佛教有很强的“取相存见”的倾向。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达摩所传禅法的最大特点却是,法于“虚宗”,存“遣荡之志”,舍“罪福之宗”,“玄旨幽赜”,“理性难通”(以上《续高僧传》“习禅论”语)、“情事无寄”(“慧可传”语)、“忘言忘念,无得正观为宗”(“法冲传”语),所以可以想见,这种禅法实际上应该是很难让北朝的朝野上下所理解和接受的,因而受到讥谤也就在所难免了。昙林所说的来自于“取相存见之流”的讥谤,指的应当就是这个。
不过达摩在魏地,似乎一直待在嵩洛一带,在僧副、慧可等人从达摩受学的时候,北魏的朝廷也尚且远在平城,嵩洛还不是北魏佛教的中心,所以那个时候还不至于受到太多的讥谤。但是自太和十八年(494)迁都伊洛,大批僧侣亦随之南迁,嵩洛一带一跃而成了北魏佛教的中心。这样,朝廷上下的重功德、福田、饶益的风气自然也就顿时倾动了嵩洛一带,而达摩的罪福两舍、“情事无寄”、“理性难通”的禅法自然也就要遭到白眼了。后世的灯史,如《传法宝纪》、《历代法宝记》以下等皆谓有人曾多次毒害达摩,这当然不一定是事实,但此说之所以会出现,显然是意味着当时达摩系统的禅师,因为所持的见解不同,而受到了较为激烈的讥谤甚至于排挤和迫害。乃至过了几十年之后,到慧可出世传禅的时候,还依然因其说法是“情事无寄”而遭到迫害。并且,如《续高僧传》所说的“多生讥谤”那样,讥谤肯定是来自于多数和多方面的,大有群起而攻之之势。因为处于这种环境之下,所以达摩及其弟子们当然也就难以继续居止于嵩洛一带传习禅法,所以达摩便要“不测”、僧副便要南游、慧可便要隐迹埋形——这些都应该认为是与魏都南迁、北魏的佛教中心移往嵩洛一带有直接的关系。所以,495年这个时间,显然是有相当的根据的,应该是可信的。而且由此来看,达摩于495年“不测”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灭化”的可能性。
与达摩495年“不测”或“灭化”的时间是可信的一样,慧可于达摩“不测”或“灭化”之后隐居四十年之久,也应当认为是可信的。这不仅是因为两说本是相互关联的,而且还因为,自北魏迁都伊洛(494)至东西魏分裂(534)也正好是四十年。这四十年间,慧可经过在皖山的隐居修学之后,又返回北方,隐于洛下,“默观时尚”。及至北魏经历了种种内忧外患而分崩之后,事实已经证明,“取相存见”的北魏佛教,实际上是禁不起现实考验的,北方的佛教已经到了应当开始一个新时代的时候了。于是,慧可便离开了“取相存见”的势力依然强大的伊洛,到新邺去公开传授他的禅法。这四十年的时间,与历史的进程也正好吻合。所以,隐居四十年之说应该认为是可信的[15]。
达摩既然应该是在495年时离开魏地,而如果慧可初遇达摩时已经有四十岁的话,则两人分手的时候,慧可就应该是四十六岁(跟随达摩的时间是六年)了。若如是,则其出生就应该是在太平真君十一年(450)。然而《续高僧传》说,周武灭法时(574)慧可曾与同学昙林共护经像,若真是太平真君十一年生,至此时就应该有一百二十五岁了。如此高龄,在僧史上当是罕见的,碑记、僧传、灯录总该有所言及[16]。然而,毕竟何处都没有这样的记载,所以我们可以断定慧可肯定不会住世到一百二十五岁的高龄。因此,也就可以断定慧可初遇达摩的时候,不应该是四十岁,而应该是十四岁。“十四岁”,与《续高僧传》的“年虽在后”、昙林《二入四行论序》的“年虽后生”之说正好吻合,可以相互印证。这样,495年两人分手时,慧可应当是二十岁。则可推知,他应该是出生于北魏孝明帝的承明元年(476)。
慧可与达摩分手时,因为年纪尚轻,受道未久,尚需进一步修习;同时,又须回避“取相存见”之徒的讥谤和迫害,所以就隐身埋名去修学了。《续高僧传》说,慧可在遇达摩以前,已经是“外览坟索,内通藏典”了,后来又“怀道京辇,默观时尚。独蕴大照,解悟绝群。虽成道非新,而物贵师受,一时令望咸共非之”。但“权道无谋,显会非远,自结斯要,谁能系之”,这显然是因为道宣以为慧可四十岁时才遇达摩,所以才这样说。其实,其所说的“独蕴大照,解悟绝群”、“成道非新”、“自结斯要,谁能系之”这些事情,显然讲的应该都是得达摩传授而开悟之后的事情,而不应该是得达摩传授之前的事情。不过,我们由此可以知道,慧可在与达摩分手之后,在依《楞伽经》修学的同时,还曾广学内外经论,最后隐居于洛下,默观时尚,以待出世度人的时机。因其“独蕴大照,解悟绝群”,所以自然会引起时人的注意。但当时有名望的僧侣们一旦知道他的禅法是师承达摩,就又开始排挤他了,即所谓“物贵师受,一时令望咸共非之”是也。然而,正如道宣所说,此时的慧可已经是“成道非新”、“久结斯要”(开悟见性)的人了,又有谁能遮障得住他呢?所以,渐渐名声远闻,道俗渐渐地汇集于他的周围,愿为其弟子,从其修学。这里须注意的是,道宣提到了慧可传禅的特点乃是“言满天下,意非建立,玄籍遐览,未始经心”,可见慧可传禅的风格已经是不立文字(言满天下,意非建立)、不重经论(玄籍遐览,未始经心)了,虽然他自己曾经是“外览坟索,内通藏典”的。
这样,慧可在洛相一带的影响渐渐地扩大。到了天平之初(534),北魏东西分崩,“取相存见之徒”失去了他们最有力的靠山,新的时代已经到来,新的佛教已经到了应该扬眉吐气的时候了。于是,慧可北游新邺,开始公开传授他的禅法(“盛开秘苑”)。然而,他的禅法毕竟是不立文字、不重经论的,是“情事无寄”的,与北朝佛教“取相存见”的传统风格依然大相径庭,所以虽然已经能够得到很多人的赞同和归信,还是引来了“滞文之徒”的“是非纷举”,乃至说他所说的是“魔语”,对他进行反复的干扰和残酷的迫害。这样,他的禅法当是又被打上了异端的烙印,使他无法继续在新邺传禅。但他却顽强地于新邺周围的地区(邺卫),继续传授他的禅法。
值得注意的是,道宣讲到,慧可在经过了这场风波之后,醒悟到众生的根机有深浅、智量有大小,听到真理,根深智大者会欣喜,根浅智小者会恐怖(始悟一音所演,欣怖交怀,海迹蹄滢,浅深斯在),所以他便随顺世间(顺俗),改变了传禅的方法。即,他想出了巧妙的方法:一是“乍托吟谣”,一是“或因情事,澄汰恒抱,写割烦芜”。前者是指作偈颂,后者的文义不明,或许是指制作一些类似于后世公案的东西。然而,他所传的禅法毕竟是“幽而且玄”,正道毕竟是“远而难希”,众生的无明妄执毕竟是“封滞近而易结”,所以乃至于他的弟子之中也没有出现倾动当世的人物(末绪卒无荣嗣)。慧可的弟子,本传之中举出了那禅师,那有弟子满禅师。“法冲传”中,包括那禅师在内,共列举了十二人,这些都是慧可门下的优秀人材。
《续高僧传》说,慧可至周武灭法时(574)尚且住世,与同学昙林共护经像。那么,即使初遇达摩时只有十四岁,这时也应该有九十八岁了。《续高僧传》没有说慧可是何时入灭的,但《景德传灯录》则谓慧可以一百零七岁的高龄灭于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这个时间虽然很明显是杜撰的,但慧可活到一百零七岁之说早在《历代法宝记》的时候就已出现,若以此年龄为可信的话,则慧可应灭于隋文帝开皇二年(582)。
五
达摩如果没有入灭,而是不测所终,那么他的去向自然就成了一个问题。
由于缺乏资料,这个问题很不好讨论。但是,有一个线索还是有必要提起,那就是,大约在达摩不在北魏的第三年,也就是齐建武四年(497),傅翕出生于乌伤(今浙江义乌)。唐楼颖所撰的《善慧大士录》中说,傅翕于梁武帝普通元年(520)二十四岁时,一日在沂水取鱼,遇一胡僧,号“嵩头陀”,发其宿因。此嵩头陀的真名叫达摩,其在乌伤一带活动的时期,即相当于禅祖菩提达摩不在魏地以后的时期,而且似乎也是专门传授禅法,风格也与慧可一派的楞伽师们的风格一样——重头陀之行。所以,这个达摩一向被怀疑为是否有可能就是禅祖菩提达摩。
《善慧大士录》(《新纂大日本续藏经》六十九卷)中有《嵩头陀法师传》,其内容大致如下:嵩头陀名达摩,不知其为何国之人,樵夫最初发现他,是在双林[17]之北四十里的香山之中。被樵夫发现之前他在香山之中似乎已经隐居很久了,但究竟有多久,没人知道。后来与梁常侍楼偃相遇,在楼偃等人的帮助之下,建了一座香山寺,颇多神异。之后,于梁普通元年(520)离香山南游,至余山(当是乌伤一带的山名),欲渡江(当是指东阳江),而江水泛滥,船家不肯摆渡,于是达摩便把伞布于水上,手把铁鱼磬,截流而渡(后世有达摩“一苇渡江”的传说,应当就是由此发展演变而来的)。渡江之后,南至稽停塘下,见傅翕于沂水中(不是山东的沂水)捕鱼,遂发其“神妙之迹”(点破其宿因),并指示其修道之所——松山双林,然后至莱山(当在乌伤与金华之间),建莱山寺,又西至金华建龙盘寺,又西至龙丘(大概就是现在的龙游)建龙丘岩寺,又西行入万善山建离六尘寺,又西行至孟度山建三藏寺。后还龙丘岩寺,并终于该寺。《善慧大士录》中暗示嵩头陀灭于天嘉五年(564),但《嵩头陀传》中并未说其灭度于什么时候,只是说他曾对傅大士说他“不值菩萨道兴”。据此,则他实际上应当是灭于傅大士入见梁武帝的中大通五年(534)十二月以前。
此传中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法师号“嵩头陀”。这个称号,其本人自己如果不说,别人本来是不会知道的,因为当地的人是不可能知道在嵩洛传禅的菩提达摩的事情的。而且他甚至没有说自己是哪国人,却告诉人家自己号“嵩头陀”,好像这个称号比国籍还重要,这正说明他是在向人暗示他与嵩山的关系。
第二,“嵩头陀”又名达摩,这更进一步向人暗示了,他就是曾在嵩山行头陀行的达摩——菩提达摩。但是,当地的人既然不可能知道嵩洛的菩提达摩,那么这种暗示,与其说是对当时当地人的,倒不如说是对后世人的。所以这就意味着,这个“嵩头陀”的传记,至少关于其名号的这一部分,有后世假托的嫌疑,因而也就没有值得完全凭信的价值,因此我们也就无法推测这个“嵩头陀达摩”是否有可能就是禅祖菩提达摩。
第三,虽然我们尚且无法推测“嵩头陀”是否就是禅祖达摩,但从《善慧大士录》本身的暗示来看,至少从唐代开始就已经出现了试图将二人联系在一起的倾向。后世所盛传的达摩“一苇渡江”的传说,显然就是从嵩头陀“布伞江上,截流而渡”的传说演变发展而来的。两人之所以被联系在一起,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嵩头陀点化傅大士的方式和被嵩头陀所点化的傅大士的风格,与禅宗传法的方式和禅宗风格有极为相似之处。这一点,在我们探讨达摩的禅法的时候,将会提供给我们很多可供参考的线索。
(本文所用的资料中,《续高僧传》、《楞伽师资记》、《历代法宝记》、《景德传灯录》、《洛阳伽蓝记》,用《大正新修大藏经》本;《祖堂集》、《宝林传》用中文出版社影印本;《善慧大士录》用《新纂大日本续藏经》本。由于篇幅之限,就不再详标卷数页数等出处了,请谅解。)
注释:
[1]一般认为《洛阳伽蓝记》的资料为有关达摩的最早史料,但本人对此持有异议,详见下文。又,按理说《楞伽师资记》所收之昙林的《二入四行论并序》当更早,但因《楞伽师资记》成书较晚,所以一般皆不以昙林的《二入四行论并序》为最早的史料。
[2]但是《楞伽师资记》则说达摩是“泛海吴越”,指的是浙江沿海一带。现在已经无法、也没必要去追究达摩最初究竟抵达的是南越还是吴越,但总之,他最初是从海路到达中国的南方是不会错的。不过,正如后文将要提到的那样,嵩头陀达摩活动的地方在吴越,若与菩提达摩是一人的话,则达摩最初到达的地方很可能是吴越——毕竟与此地缘深。
[3]从《历代法宝记》开始,灯史中出现了达摩北度之前与梁武帝相见的传说,从时间上来看,此传说大概不会有史实为依据,所以在此就不予讨论了。但有一点可以作为备忘,即达摩虽然不会在南朝与梁武帝相见,但完全有可能在北朝与孝文帝相见。南朝佛教重般若,北朝佛教重功德利益,所以达摩说造寺度僧“并无功德”,不应该是对着梁武帝的,而应该是对着北魏孝文帝的。
[4]据此可知,达摩至魏后,最初是隐栖禅居于岩穴之中,并未入都市行化。岩居的地方大概就是在嵩山。后世传说达摩曾在嵩岳的石洞中面壁九年,应该就是根据此事而来的。

[5]据此则达摩的禅法于六世纪初就已经传入四川了。
[6]佛家有所谓依止法,即出家之后,至少五年之内,依本师而住;五年之后,经本师许可,可以游方。
[7]“周历讲座,备尝经论”的时间究竟有多久,实难确定,不过至少也得要三、五年的时间吧。
[8]此与昙林的《二入四行论序》所说的有所不同,昙林谓“亡心寂默之士,莫不归信;取相存见之流,乃生讥谤”,并非定指讲授之徒。
[9]印顺法师等人认为,古人有时亦泛指天竺为西域、印度人为胡人,如昙林即称“西域南天竺”即是。印顺法师又引证,古时被译为“波斯”的不止一处,南海之中即有“波斯”两处,则南天竺或者亦可能有“波斯”。此说虽非无其理,然未免牵强,不如就近取据。
[10]见《胡适说禅》82页,东方出版社,1993年。宇井伯寿《禅宗史研究》16页,岩波书店,昭和41年。印顺《中国禅宗史》第3页,正闻出版社,民国81年。
[11]有人因此而对后世的灯史将僧副列入达摩弟子之列,表示不以为然,是不对的。
“慧可传”中未言及僧副,显然是因为道宣所得到的达摩和慧可的资料中未言及僧副的缘故。但是,这只意味着这些资料中未言及僧副,而并不意味着僧副之师“达摩”不是禅祖达摩。按,僧副应当是达摩在魏地所度的最早的弟子,而且数年之后,便离师游学,所以道育、慧可等从达摩修学的时候,僧副即使尚在达摩身边,不久以后也就离师游学去了,这样,慧可和昙林对僧副的事情,既不见得会知道多少,也不见得会有很深的印像,况且僧副后来又远游江南,一去不回,并且又早逝于524年,与后来在北方弘扬达摩禅法的慧可等人毫无关系,所以慧可、昙林对其无所言及,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并不妨碍僧副本是菩提达摩的弟子。其次,道宣在“僧副传”中未明言僧副是菩提达摩的弟子,应当是因为他未得到确实的资料,不能率尔便将二人联系在一起。究其原因,大概是道宣所得到的僧副的碑记资料中未说清楚。僧副的碑记,当是作于南方,关于他的师承,只能是根据他自己生前所述。但是,对于菩提达摩师徒在北方受到讥谤甚至排挤迫害的事情,他应当是有所讳言的,所以不便说出其师全名——菩提达摩,只是含糊地说师名达摩,而他的碑记也就如是记载了。所以,这并不妨碍他就是菩提达摩的弟子。再者,僧副从达摩学,是在大约486—490的时候,此时在魏地活动的达摩禅师,只能是禅祖达摩。所以,僧副理所当然地应该是禅祖菩提达摩的弟子,这一点是不应该有问题的,只不过是道宣未能将此点澄清而已。
[12]据印顺法师《中国禅宗史》(页44)说,[山+皃]字当为[山+完]字之误,[山+完]亦同皖字。皖山在今安徽省潜山。
[13]此说意味着,达摩在魏地最多只待到太和十九年的495年,而495年以后,不管是灭度还是他游,反正已经不在魏地了。这一点,从又一个侧面提供了《伽蓝记》的菩提达摩不是禅祖达摩的证据。
[14]《历代法宝记》说慧可在达摩灭后“四十年隐[山+皃]山洛相二州”,据此说,则慧可与达摩分手后,先隐于[山+皃]山([山+皃]字为[山+完]字之误)。此山在今安徽省潜山,故知慧可当时亦曾离开魏地南下,只是未如道副渡江而已,而且后来又返回魏地,隐于洛相之间。
[15]达摩灭后?慧可不得不一直隐居了四十年,才公开出世传禅,这亦可见达摩一系的禅法在北魏的生存环境之严酷。
[16]《景德传灯录》更谓慧可以一百零七岁灭于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若真在开皇十三年入灭,那就应该有一百五十岁了,怎么还会只是一百零七岁呢?所以,开皇十三年灭度之说,显然是杜撰的。
[17]在乌伤(今浙江义乌)之松山,就是傅大士后来结茅修行的地方。